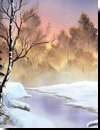 【摘要】山水文学从来不是自然风景的录象带,只要加上一个“美”字,就不可能没有人心在自然风景上的投影。人类把自己被大自然陶冶出来的性灵,又反馈到青山绿水中去。他的要素则包括哲理的、性情的、意气的三个方面。任何成功的艺术都不能脱离作者的性情,山水文学也不例外。山水文学的创作,就其作者来说,离不开他的实际生活,人生经历,不能单靠一次游览写出不朽的作品。山水文学要想超出习作的水平,依赖哲理的抉发来提高审美的层次是其一,按照性情的投(投影)合(融合)丰富审美的内涵是其二。趁着意气的激荡扩充审美的表现是其三。中国的山水文学,特点是不停留在自然主义的描写水平上,提高的办法是以性灵加工山水,而性灵又恰恰来自山水的陶冶。哲理也好,性情也好,意气也好,不全是社会的产物,大自然也参与了工作并引起了反馈,正如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美的组成部分,自然美也是社会影响的一个能动的环节,二者的辩证结合。 【摘要】山水文学从来不是自然风景的录象带,只要加上一个“美”字,就不可能没有人心在自然风景上的投影。人类把自己被大自然陶冶出来的性灵,又反馈到青山绿水中去。他的要素则包括哲理的、性情的、意气的三个方面。任何成功的艺术都不能脱离作者的性情,山水文学也不例外。山水文学的创作,就其作者来说,离不开他的实际生活,人生经历,不能单靠一次游览写出不朽的作品。山水文学要想超出习作的水平,依赖哲理的抉发来提高审美的层次是其一,按照性情的投(投影)合(融合)丰富审美的内涵是其二。趁着意气的激荡扩充审美的表现是其三。中国的山水文学,特点是不停留在自然主义的描写水平上,提高的办法是以性灵加工山水,而性灵又恰恰来自山水的陶冶。哲理也好,性情也好,意气也好,不全是社会的产物,大自然也参与了工作并引起了反馈,正如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美的组成部分,自然美也是社会影响的一个能动的环节,二者的辩证结合。
【关键词】山水文学性情哲理意气。
【正文】
论山水文学中的性灵加工
我国的山水文学寻起根来固然很早。《诗经》里已经有了“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楚辞》里已经有了“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些都已经有了形象思维。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已经有了分析和评价山水之美的抽象思维,理论上应当看作山水美学的始祖。但是,真正的中国山水文学兴起在中古,即刘勰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的年代。谢灵运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人。“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橙鲜”等对自然景物作精细、形象的描绘,表现出对某一景观的情思韵味,朝着景物与情思交融的方向发展,传达出诗人心中一种难以言喻的对生命的惊喜。范文先生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早熟的,一开始就有性灵加工的文学。他的要素则包括哲理的、性情的、意气的三个方面。这个历史性特色的现实意义,在于新的山水美学,必须走出书斋,与游人所需要的美育互相促进。中国的山水文学,特点是不停留在自然主义的描写水平上,提高的办法是以性灵加工山水,而性灵又恰恰来自山水的陶冶。
山水文学从来不是自然风景的录象带,只要加上一个“美”字,就不可能没有人心在自然风景上的投影。人类把自己被大自然陶冶出来的性灵,又反馈到青山绿水中去。这事没有相当程度的个性发展,显然是办不到的。它的标志是游人在数量上、质量上的提高。
游人数量的提高,在空间上依靠交通工具的发达,在时间上依靠闲暇消遣的方便。左思生在晋朝,他在《三都赋》里提到“户藏烟浦,家居画船”的盛况,虽然有些夸张,毕竟不是先秦时代所具备的。闲暇呢?它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谋生的途径多了,方式方法可以由人们自己选择了,所以在地广人稀的上古,反而无所谓闲暇了,反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至于游客数量的提高,它不仅需要文人墨客的纷纷加入,而且需要欣赏观点的日益分化。这事也发生在中古,那时开始出现了贵族型的游客,也出现了平民型的游客。谢灵运和陶渊明的山水文学各有千秋,只是谢灵运知道享受山水,陶渊明却能消化山水。换句话说,通过哲理的阐发,使物态通于心态,美育通于德育,山水观通于人生观,这种崇高的欣赏,应以陶渊明最为擅长,方为公允的评价。李白的山水诗情景交溶,韵味悠长。
李白在山水诗的创作中,最擅长于以情写景,以景抒情。在艺术表现上,诗人经常只选择自然景物中最富特征,自己感受最深的某些方面加以突出的描绘,在具有浓郁的主观色彩的氛围中,抒发了作者的性情,故而较之晋宋诗人的“情、景、理”三段式的风格情调更胜一筹,作品意境高远,感情更为真挚。例如,《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春,是现在公认的古代山水诗中最优秀的篇章。当时作者因永王璘案被流放夜郎,取道四川赴贬地,中途遇赦,惊喜交加,当即从白帝城放舟东下江陵。诗人那历尽艰险而遇赦的喜悦心境,久别亲友而归心似箭的急切念情,以及得以解脱之后的兴高采烈的神态,无不在空谷传响,夹岸秀丽的山峡风光之中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全诗气势豪爽,情景交融,精妙至极。明?杨曾赞曰:“惊风雨而泣鬼神矣”。
在具有民歌风采的《清溪行》中,作者以清新流畅的诗句,赞颂了大自然的明媚秀丽,抒发了对社会黑暗的愤懑之情:
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
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
诗人着意描述的是清溪水清如碧,清澈见底,然而却寄予了他对社会污浊混沌的愤慨,勾画出的是一个情调凄凉哀婉的清寂境界。又如《夜宿山寺》:
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从诗的语句看,诗人只是写了山中的一座小寺院,但仔细咀嚼,山寺的静穆,环境的净谧,以及超脱凡世喧嚣的佳境,都给人以充分想象的余地。味外之旨,正是作者抒发的厌弃世俗,向往自由的情怀。同样,《山中问答》也是一首含蓄蕴藉,情趣盎然的佳作: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这首诗以问答形式抒发了诗人隐居山林的闲情意趣,语出自然,浑然天成,秀雅的画面,色艳景幽,情真意远,韵味之美,意境之美,使人陶醉。再如《寻雍尊师隐居》: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计年。
拨云见古道,倚树听流泉。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满是云雾的山林,是那样的幽静,在云雾中行走,是那样的闲逸。诗人成功地捕捉了他对自然景物、山光水色的独特感受,以刻练之笔出以平易面目,在继承谢灵运、谢眺、何逊、阴铿等前人的基础上,加以了更深层次的开拓。《岁寒堂诗话》云:“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乃诗人之余事。”
李白有的诗,虽通篇不以写景为主,但以一二写景语而显得情景交融,韵味悠长。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抓住孤舟远影没入水天之际的动人景色,造就一种高远无穷的意象,表现出对故人的无限神往。它如《听蜀僧浚弹琴》中的“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夜泊牛渚怀古》中的“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等,诗人仅以一二写景之语,即穷形尽相地描状了景物,真切地显示出了自然景物的特征,深沉而含蓄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挚感情,它们都给人们以美好的艺术享受,对于山水风景诗的发展有所贡献。
任何成功的艺术都不能脱离作者的性情,山水文学也不例外。同一山水在人心得到的投影可以千差万别。譬如同一个剑门山路,在李白是“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陆游却是“此身合似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难道剑阁的险阻,一变而为清秀可亲吗?同一个洞庭湖,在孟浩然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那样逼人而来,在李白却是“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那样听人抚弄。固然湖水的或动或静略有不同,但不会有根本的不同,差异还在作者的兴致。再如杨柳的形象,在萧悫那里是“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在李商隐那里确是“絮乱丝繁天亦迷”难道为了给李商隐的繁乱以实据,非得把萧家的杨柳改为密植不成?同一景物,只要里面包含的角色,即所谓诗中人换了样,描写的方式就会大大改变。如范仲淹《苏幕遮》词里的“碧云天,黄叶地”,和王实甫《西厢记》里的《端正好》一阕的“碧云天,黄叶地”,愁人愁景没有不同,只是前者是思乡的客子在意境中隐现,故愁肠绵远,后者是惜别的恋人在意境中隐现,故愁肠切近。于是接下来的描写便不一样了;在范仲淹那里,下文是“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的远景头。在王实甫那里,下文是“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的近镜头。反过来映照起笔的是:范仲淹以云天为近景,先抬望天色,再远眺那通往家乡的烟波,王实甫以云天为远景,先环顾这千舍万难的郊野,再往身边拉近,几乎要把那些散在各处的红叶都拉倒心坎上来。同一片云,用之于近则近,用之于远则远,只是人心得到的投影不同罢了。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特色就是在山水风景的描写和记录里,不声不响地寄寓以至抒发了作者的性情。滁州之地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风景,欧阳修却赋之以高士逸民的个性,山亭附近的四季风光被他写成挺拔不群,睥睨俗物的胜地。他在另一篇文章里,直截了当地表明,山水之美必须适合他的性情。在醉翁亭上,那些“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酒使他的尘虑纷扰得到缓解,专心爱美得到浇灌,轻快地沉浸在自然美里。平时不甚出奇的景色,这是由于心境的专一,触发了新的美感。那是纷驰在表层,来去匆匆的心潮所无从捕捉的东西。你看,一座城的周围有几座山,山中有几许溪泉,这有什么稀罕呢?峰回路转算得什么?天下哪有笔直的山路?说什么走近了才听见溪流的声响,远了你听的见吗?这一堆毫无特色的东西,别人比不过问,欧阳修一来就立刻趣味横生。为什么?因为有欧阳修的性情在。不信你看:“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泻”字选择的多么恰当,它既不是太强又不太弱,令人想见欧阳修下马登山,既不急来又不缓,只是一路上寻声觅径而抵源头,有如晚唐诗“夜声寻彻碧潺潺”之以声音表达出情态。你也别把那几个“也”字随便放过。他们特别适合探询者半惊讶的语气和神色,而半惊讶正是胸有成竹而居然找到者的必有之态。不要说山水本是无情物,他会跟着主人的性情改换面貌的。当然山水不止一位主人,他有许多主人聚集在一起。人民是山水的主人,所以和山水相融的性情,不限于一个人的性情,而是联系到当时的社会风尚的。欧阳修的前辈王元之在滁州的时候,作了《唱山歌》一诗,他写到:
滁民带楚俗,下里同巴音,
岁埝又时安,春来恣歌吟。
接臂转长环,聚首丛如林,
男女互相调,其词非奔淫。
可见人民在行路和劳动中,用歌声彼此应和,滁州本来就有这种民风。因此欧阳修把它写进《醉翁亭记》,以示太守之与民同乐。这样,性情的融合才更加淳厚。我们说山水文学离不开性情,不是单指个人的性情。最好把时代的风尚和民俗,都表现在山水文学作品里去。
山水文学的创作,就其作者来说,离不开他的实际生活,人生经历,不能单靠一次游览写出不朽的作品。山水文学要想超出习作的水平,依赖哲理的抉发来提高审美的层次是其一,按照性情的投(投影)合(融合)丰富审美的内涵是其二。下面要说的,趁着意气的激荡扩充审美的表现是其三。这事以柳宗元的山水文学为例。
柳宗元不想陶渊明那样“少无适俗韵,性本爱邱山”。他对山水的爱好是他在人生的道路经历坎坷之后的事。年少时他攀附权臣,希图富贵,说得好些是事业功名。短命的李俑(唐顺宗)信任宦官,妃妾,和翰林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共参谋议,互相推奖,其门“车马如市”。不久顺宗病重,传位太子(唐宪宗),而太子讨厌他们,一登基就把他们贬斥。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一肚子学问无处发挥,就发挥到山水上去了。于是千古争传的游记,“永州八记”问世了,一批山水诗也完成了。其实永州并没有什么可观的山水。明朝的文豪茅坤崇拜韩柳文章,熟读永州八记,一心向往,乃至亲赴永州,一看究竟,结果大失所望。原来柳宗元赞不绝口的竟是一堆毫不起眼的山丘,什么“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什么“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根本没有那回事。那么柳宗元为什么要那样描写呢?用韩愈的话来说,是“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久为簪组束,幸此南夷谪”。一句话,意气的激荡使之然。可观的时势,主观的遭遇,那激荡之气当然在于主观,所以柳宗元的山水文学,特重写意。若是一笔一划地给自然美作记录,那激荡何时得平?永州既没有奇观,他又不能丢官弃职去同览四海名山大川,只好就此写意罢了。
西洋学者说,“在中国的绘画里,远山,浮云,湍流,安详的河水,幽深的山池,都好像寓居着一种看不见而又很真实的东西”。柳宗元的游记也是这样.他所记的本来就不是山水的副本,而是以山水的陶冶谱写他的抒情小曲,这是和单纯游记家的游记,如《徐霞客游记》,略一比较便可看出的。柳宗元决不由于永州没有与天相际的峰巅,就搁笔不写他在峰巅的感受;既在意气的激荡之下,就谈不到拘执末节;他干脆就自己性之所近来接受大自然的美育就是了。他在《零陵三亭记》里写道:“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宇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意思是有了美育,人们才不致局促在生活的物质限制里。柳宗元离开金碧辉煌的朝堂,来和农夫,野老,山林,云水相过往,以“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的简朴生涯自娱。那鱼和酒未必满足他的生活需要,却无疑地满足了他的意气,这就成了他从新接受美育的端倪。例如他在《南涧中题》里所写的“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是一种动中观静的境界,不能从繁华的环境体验到的,新美育的成效也就于此显示。
细读柳文,还可以看到自然美虽然常住,对人却不是一成不变的灌输。而是以其变化不尽的细节,多种多样地来丰富人的感受,例如他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里写道: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山甚〕,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短短的一段游赏却有三桩变化。起初写风景十分清秀;中间错杂多姿,点缀生动,而略感空旷;末尾则一片凄清之感。实则咫尺未移,时间也不过一个下午,而且始终有他们五个人在,偏说寂寥无人。可见这全是从心目中写出的感受,不受客观实录的限制。柳宗元深知人是自然美的成分,不能把欣赏者本身排除在欣赏之外,而这是相当高超的审美能力,通常很难办到。他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若不把自己的化身──渔翁放进去,形成我看寒江天看我,一点蓑笠六合间的大自然舞台效果,怎难把三千银界,所向光明的境界表现出来呢?
我们不妨估计,把一人一舟,通常被写进微观的情景,放大到无垠无际的宏观里去,如此宽阔的眼界,大概是柳宗元意气激荡的产物。不过他有个审美修养作为前提,那就是要自然陶冶你,首先你得尊重天造地设的天然产物。在《钴鉧潭西小丘记》里,柳宗元高瞻远瞩而又心扉密合地指出:“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鱼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然而万化冥合在心神之际,别看他说得多么神秘,其实是一种精神状态,回落到现实,乃是自然与人工合作完成的美育,也就是柳宗元在《序饮》里所说的“合山水之乐,成君子之心”。他把大自然看成一本硕大无朋的美育教程,不肯轻易如意涂抹。他只是“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坠之潭,有声淙然,尤于中秋观月为宜(见其《钴鉧潭记》,所动用的人工不过如此。在《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里,他更明确地提出“决浍沟,导伏流”的工作,使之“散为疏林,洄为清池”还说那是“若造物始判清浊,效奇于兹地,非人力也。”这表明了他的理想境界,即使动用了人工,还能和不曾动用一样,在自然美和人工美之间,左右逢源。当然,这事不容易办到,没有现成的方案,只能在探索中前进,但意气激荡之不等于逞意胡为,焚琴煮鹤,则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中国的山水文学,特点是不停留在自然主义的描写水平上,提高的办法是以性灵加工山水,而性灵又恰恰来自山水的陶冶。哲理也好,性情也好,意气也好,不全是社会的产物,大自然也参与了工作并引起了反馈,正如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美的组成部分,自然美也是社会影响的一个能动的环节,二者的辩证结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