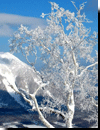 生命最后那段时间,要依靠杜冷丁抵抗身体的疼痛,她明显感觉这些难熬的日子越来越漫长,而打杜冷丁的时间间隔一次一次在缩短。寒冷的冬天,窗外却看不见一丝雪白,她能看见的只有空旷的天空,干枯的树枝,和几片在风中摇晃的黄叶。能感觉到只有干冷的空气和呼啸的北风,它们似乎时刻要熄灭她日渐微弱的生命火苗。 生命最后那段时间,要依靠杜冷丁抵抗身体的疼痛,她明显感觉这些难熬的日子越来越漫长,而打杜冷丁的时间间隔一次一次在缩短。寒冷的冬天,窗外却看不见一丝雪白,她能看见的只有空旷的天空,干枯的树枝,和几片在风中摇晃的黄叶。能感觉到只有干冷的空气和呼啸的北风,它们似乎时刻要熄灭她日渐微弱的生命火苗。
她早就安顿好了女儿和母亲,嘱咐好了丈夫。然后就静静地躺在床上,守着枯竭的生命。家人和朋友同事都日夜陪在她的床前,怕她寂寞,所有陪过她的人都悄悄地流着泪,她太年轻了,她只有三十四岁,却患上了让人色变的绝症,她头疼得厉害,可恶的癌细胞已从肺部扩散到了大脑,就在确诊的二十天后,她就必须依靠杜冷丁来镇压来自身体内部的剧烈的疼痛了。
川流不息的来陪她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眼睛每刻都在搜索,她的心里每时都在盘算,因为她还有一个愿望,想最后看他一眼,和他说一句对不起。
他是她心中永久的痛。
她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她的床边只有她一个最好的姐妹,她突然抓住朋友的手,泪如泉涌,把她朋友吓坏了,忙问她是不是又疼了,是不是该打杜冷丁了?朋友转身要去拿针,却被她死死的拽住,朋友惊讶地看着她,她依然泪流满面,她恳求地说:“我想见他最后一面。”朋友明白了,泪水瞬间陪她流了满脸。
朋友想尽了办法,把她家里人都支走了,她按约好的时间打了杜冷丁,之前她疼得豆大汗珠直滚,身体像洗过一样,她只想在他来之前扼制住疼痛,以便给她更多的时间,她只想把最好的一面留下来。她认真仔细地梳洗,打扮一新,等着他的到来。
他已经从家里走出很久了,他没有戴帽子,甚至羽绒服的拉链都没拉上,在这干冷的空气里,人们都来去匆匆,向踌躇的他投来一瞥的不解,然后自顾走过。
天是阴沉的,如他的心情,他已经犹豫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他的心里一直是怨她的,直到昨天有人告诉他她得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想在生命最后一刻见他一面,那人说得恳切,他对她多年的怨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他是名船员,他们认识的时候就是,每年四月开江出航,一直到十月末封江才能回来,他们相恋了三年,在说好封江结婚的那一年十月,他回来的时候,新郎却不是他。
他没有去问理由,不用问,那年月,船员是找不到妻子的,许多船员的妻子都是农村来城里打工的,没有城市户口的,或者城市里没有工作的人。似乎这一切已成了定律,兄弟们在外摸爬滚打半年多,照顾不了妻儿老小,所以没有人愿意把自己与一名船员的生活捆绑在一起,甘心情愿地承担本该两人承担的家庭重任。这些他理解,所以他不去问,只把自己埋藏在一团烟雾中,对她当初信誓旦旦的誓言充满了怨恨。
那年冬天,经人介绍,他与一个打工的农村姑娘结了婚,婚前只见过三次面,他是出于报复她的心理,他想他这一生就会在没有爱情中渡过。妻子的善良、勤劳、温柔、体贴慢慢融化了他冰冷的心,紧接着是可爱的女儿的到来,他才渐渐地对家庭,对妻子,对女儿有了爱意。
许多年过去了,他平静地生活,只是偶尔想起她来,仍免不了涌出一丝怨恨,是的,她伤了他的尊严,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他要站着,挺直腰板,尽管他是一名船员,每日与偌大的船舶打交道,机器整日轰鸣,油味刺鼻;整日穿着桔黄色的救生衣,起锚系缆;整日与流动的江水为伍,只要几日,就皮肤黝黑,手上沾满了洗不尽的油污;整日只与船上的工作人员交流,寂寞难挡。他都不在乎,他就在乎谁伤害他本就脆弱的尊严。
如今他已是一名优秀的船长,他的船舶年年被评为样板船舶,他也因此受到了各种奖励。
这些与她有关系,是他要证明给她看。
此刻,他迈着沉重的脚步,抬头看阴沉的天,他忽然发现天空竟飘起了雪花,这是今冬第一场雪,迟到的雪,他感觉出空气一点点由尖利的干冷变得湿润柔和起来,雪花轻盈地舞着,越下越大,雪片也变大了,落在他的脸上,融化成水滴,落到他的身上,把他的肩膀染成白色,他不知徘徊了多久,置身这洁白苍茫中,他忽然豁然了,他有什么理由拒绝一个将要失去生命、再也见不到雪花的人呢?
下雪了,雪花拍打着玻璃,好像在与她打招呼,白茫茫的世界让她欣喜若狂,她终于见到今年的雪,也是她此生最后的雪了。她忽然流泪,她觉得这是老天对自己的最大的恩赐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活在自责中,她从来没有快乐过,她恨自己不坚强,恨自己当年没有坚持说服母亲等他回来结婚,恨自己软弱地屈服丈夫优厚的家庭条件,丈夫很好,但她就是快乐不起来,多年的阴郁使她渐渐瘦弱,也埋下了病根。
她忽然清晰地听到了他上楼的脚步声,她急忙叫朋友去开门,她没有血色的脸上浮起一丝红晕,朋友诧异间,已听到了门铃的声音,当他带着一身雪白、一身寒冷进来的时候,朋友从他身边挤了出去,轻轻地把门带上了。
她多想用手触摸一下洁白、美丽的雪花啊,她伸出手,隔着玻璃,雪花滑过她干枯的手,泪水流过她发烫的脸。她终于如愿了,与他说了一声对不起,不管这一声对不起埋藏了多少年,尽管这一声对不起也表达不了她内心所有的愧疚,但是或多或少地搬走了压在她心中的重荷,她有了喘息的机会,她轻松地叹息。
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抬起手臂打开窗户的动作让她汗流颊背,窗户开了,雪花飞舞进来,一股冷气吹得她浑身颤抖,她已感受到她身体里排山倒海的疼痛涌来,她在寒冷中微笑,她自由地呼吸这纷飞的雪所带来的清新的空气,她从来没有这么轻松,她感到身体的疼痛把她压缩得很小、很轻,她感到她身着一袭白衣,变成了一朵美丽的雪花,她飞走了,带着她的痛,她的憾,她的愿,带着他的气息,她飞走了,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断续的雪一直下了几日,直到她的骨灰被安置在苍松翠柏的黄山公墓,才像有意似的停止脚步。他是在她的家人都离开后,才踏雪而来,踩着松软的雪发出的声音在静默的山上传出很远很远。
他给她带来一束洁白的百合,放在她的相片下,他真的不怨她了,她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还能说什么,他愿这洁白的百合给她的路途带来安详,希望她独自不寂寞,希望她在天堂里能够快乐起来。
他离开的时候,雪花又飘起来,他感觉她正随着风雪跟在他的身后,等他回头看时,却只是白茫茫一片,满世界只有纷飞的雪在飞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