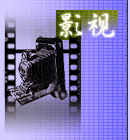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 编者按:被商业片熏陶惯了的我们,看记录片的机会越来越少,也逐步丧失了领会其深意的能力。若要改变现状,便需要创作者和观众双方为此付出更多实际的努力。 |
|
阿巴斯说,他喜欢的纪录片,是能够让人睡着的那种。这应该让很多观者难以接受,一部片子让人睡去、醒来几次,也是比较难的,因为大家早已不会因中途离场感到难为情。在刚结束的广州纪录片大会上,很多人应该有打盹或离场的经历,我就在其中一场放映中睡着了。
纪录会是不是都是那么的闷,发挥着各自催眠的效用?这个问题不用回答,因为在观影经历中,我偶然地撞上了有趣的、同时防止我打盹的片子和导演,而张以庆该是其中之一。
在谈到阿巴斯时,张以庆说他不喜欢阿巴斯的东西,张以庆坚持着“先好看,再深刻”的原则。《舟舟的世界》、《英和白》以及《幼儿园》都有着“抑制”睡眠、引起观者警醒或思考的东西。比如《舟舟的世界》里充满着稚趣的舟舟在挥舞指挥棒时的专注,比如《英和白》中人和动物之间的相处和依赖,比如《幼儿园》描述的童真以及在童真之外的追问,在充满了意趣的同时,都适当地留有思考的空间。最明显的是《幼儿园》引发了阵阵笑声,笑是因为有趣,有趣而生笑,显然是因为观众因此产生了共鸣。
当然,单纯、有趣的纪录片肯定是不让人不满足的,纪录片在有趣之外必须承载思想。对现实的尊重和责任,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纪录片的良心。吕新雨在《纪录中国》就说过:“如果我们把纪录片当作故事片一样理解,只看它的情节,就有可能丧失掉纪录片的独立意义,丧失掉对纪录片与现实关系的反省和批判。”纪录片的内核应该是对生活真相的敏锐、勇敢的探索和质疑,是对世界真诚的思考和追问。张以庆在《幼儿园》中以细节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和情感,以影像的张力来表达自己对童年的重新关照,他发现幼儿园就是社会本身,而并非如成人追忆时的美好想象。他认为在这个对恨特别自觉,对爱特别茫然的社会里,当我们弯下腰审视孩子的同时,也应该审视我们自己。
纪录片应该和文学是比较靠近的,它们都以思想为支撑,只不过文学以文字为载体,纪录片则依附于影像。很多人都喜欢在睡觉前读上几页小说或者散文,我不知道是否为了催眠,我的理解是因为有趣——能够在睡觉之前会意一笑,并且将笑留至明日,以作清晨美好的开端。
艺术应该是亲切和蔼的,就像观世音的招牌微笑和上帝可亲的手,并不怎么设起高槛拒人千里。好的纪录片或者说我喜欢的纪录片,应该是有着有趣的面孔,有着对社会真诚思考的人生态度,而不是催眠。纪录片作者与观者的不合作,故意在中间设置一道障碍,我想这是艺术的损失,而观众大不了在剧场内补充下睡眠,聪明的创作者应该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