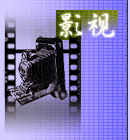编者按:一部冷色调的,低成本的,老套的故事模式的老电影;一部深刻的,令人深思的,以时间驳论为框架的探讨宿命论以及崇尚科技、忽略人性的人类未来的经典电影。
也许真的,没有人可以拯救世界,英雄只是赶上了好时候。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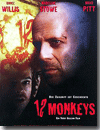 12猴子 Twelve Monkeys (1995) 12猴子 Twelve Monkeys (1995)
导 演: 特里·吉列姆 Terry Gilliam
主 演: 布拉德·皮特 Brad Pitt 布鲁斯·威利斯 Bruce Willis 玛德琳·斯托 Madeleine Stowe 大卫·摩斯 David Morse 克里斯托弗·普拉莫 Christopher Plummer Charley Scalies 莉莎·汉密尔顿 Lisa Gay Hamilton 克里斯多弗·莫罗里 Christopher Meloni
地 区: 美国 ( 拍摄地 )
评 分: 8.0/10( 67613票 )
颜 色: 彩色
声 音: DTS DTS-Stereo
类 型: 剧情 科幻 惊秫
简介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致命的病毒瘟疫爆发于美国费城,几乎同时全世界各大城市也发现同样的病例,这无药可治的病毒在短短一年的时间杀害了全球五十亿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类在地表消失殆尽。到了二零三五年,剩下的人类苟延残喘的居住在地底下,地表己经被不受病毒影响的动物们所占据。在食物和饮水的缺乏之下,人类的前途岌岌可危,为了重新回到地面,科学家们从监牢的犯人中找到了“志愿者”詹姆斯柯尔(布鲁斯威利饰),籍由时光旅行的技术将柯尔送回一九九六年病毒流行爆发之前,企图发掘当初病毒事件的真相,并找出未变体之前的病毒样本,以研发出克服此病毒的疫苗。而一切侦查的焦点均指向病毒学权威高温博士之子杰菲高温(布莱德彼特饰)所率领的“十二猴子军”,一个保护动物权益的地下革命恐怖组织。在侦查的过程中,柯尔遇见了心理医师凯瑟琳蕾莉(麦德琳史道威饰),她起初并不相信柯尔是从未来世界来的人,但后来相信了他并决定阻止十二猴子军的行动。
未来的世界显得阴暗、老旧,科学家在充满了夸张复古造型仪器的实验室中进行时光旅行实验,主角裸着身体包在大试管之中,有如白老鼠一般。反之地表上充满了过去人类的遗迹,黑熊出现在市街上,狮子攀爬于高楼顶端,对照着一九九六年的人们任意地对动物进行实验。于是二零三五年,一小撮寄居于地下仍然相信科学能拯救一切的人们与其所创造的世界,正是今日恣意玩弄自然消耗资源的人类未来的墓碑。九六年末日来临前费城的角落,不经意处布满了疑似宣告人类灭亡的警语,荒凉的街道废弃的戏院,疯子与流浪汉游荡着,不知其未来命运的人类正身处在现代的巴伦比之中。
吉连擅长描写的现实和虚幻,理智与疯狂也是本片的重点。主角柯尔如同吉连以往作品的主人公一般,游移在真实与幻像之间,梦中总会出现相同的场景,现实中常会听到不知从何而来的说话声,看到不知从何而来的人。这也许是因为被注射了药物,也许是时光旅行的后遗症,也许是因为长久未曾见到阳光,处在阴暗拥挤的地牢,失去了一切对未来的希望,或是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时空错置竟产生了不知身在何处的错觉。有趣的是,主角在一九九六年口中有关末日的预言,被他人视为是疯言乱语,而将他关在精神病院之中。心理医师蕾莉在发现柯尔的真正身份之后,也开始被其他人当作神智不清。到底疯狂的是知道未来真相的柯尔和蕾莉,还是通往毁灭而不自知的其他人?讽刺的是十二猴子军的领导者高温正是一般人所认为不折不扣的的疯子,满口语无伦次,脑中充满天马行空的奇想和疯狂的计划。无论是笃信科学还是反对科学,疯狂的城市载满疯狂的人们通往毁灭之路。
于是在各种折磿与徒劳无功的努力之后,柯尔想开始相信自己真的如大家所说的疯了,想相信二零三五年的地下世界是不存在的,想把自己当做是活在九六年的人类,放心恣意的去大吸一口空气,梦想着去看看从未看过的美丽海洋。如此本片剧情可以视为主角在体制、历史、科技的压迫混乱之中努力找寻归宿的过程。来回在没有标记的时光旅程之中,在现实中不可能有出路的情形之下,逃避现实遁入幻想成为唯一的救赎。
《12猴子》的编剧为大卫皮柏斯(David Peoples),曾经编写过经典科幻片《银翼杀手》(Blade Runner),这次《12猴子》同样也是改编自他人的原着。原作为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在一九六二年的一部二十八分钟充满静态画面的黑白短片《La Jetee》(法),故事一开始为主角的幼年目睹某一男子的死亡,而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主角存活了下来,他被时光旅行的实验送往未来及过去,到最后他才发现梦中时常出现幼年见过的景像,竟然是他自己的死亡。这样时空轮回的宿命悲剧成为《12猴子》剧情的主轴,将之延长为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加入了十二猴子军及病毒等离奇难解的谜团,以及不同时空复杂巧妙的连接,并着重在于导演泰瑞吉连所擅长执迷于理智或疯狂的人性描写。
原作中引人沈溺的感伤诗意,时空中飘浮不定之感,使得片中的世界成为一迷人诡谲的历史拼图;十二猴子军的线索,柯尔梦中幼年的场景,蕾莉不经意的从一次大战的照片发现柯尔,柯尔幼年的记忆往事是蕾莉尚未经历的未来。总总奇妙的拼贴组合累积成一连串似假还真的荒谬情节。在时间轮回的逻辑之下,所有的疯狂幻想荒谬现实都化成永不停止的宿命,在故事的尾端,梦中的儿时景像成真,动物离开笼子爬上了高速道,预先宣告着人类悲剧的降临,此时主角个人的悲剧已告一段落,他只是人类宿命下的牺牲者。就如同《La Jetee》最后主角发现的定律:谁也不能逃离时间的掌控(there was no way to escape Time)。
相关评论
一、长久以来,美国导演特瑞·吉列姆(Terry Gilliam)一直是我最敬爱的在世电影艺术家。吉列姆至出道始,从未获得过任何一个重要电影节的主要奖项,他不但游离于好莱坞的主流之外,也不入欧洲评论界的法眼。然而全世界热爱他的影迷不计其数,影迷在网上为他建的殿堂“特瑞·吉列姆爱好者杂志”,内容之详尽是我迄今之仅见;以高品位著称的DVD出版商克莱特伦(Criterion)公司已发行了他的两部影片《巴西》(Brazil)和《时间强盗》(Time Bandits),当代导演中享有这一殊荣的寥若晨星,即便如阿巴斯、大卫·柯能堡和马丁·斯科西斯也仅有一部作品入选。其中《巴西》一片更是破天荒的受到特殊礼遇,由克莱特伦精心制作了三张内容丰富的DVD碟片,更获得当年的DVD出版大奖。
我个人与吉列姆的相遇发生在1997年。这张名叫《十二只猴子》(Twelve Monkeys)的碟片从此永久的留在了我光盘包里。在几年的时间里我重温此片不下十次之多,并且不厌其烦地向所有爱好电影的同道推荐。《十二只猴子》于我而言已不再是一部电影,而是通往波普所谓“世界3”的一扇大门。这个极端复杂、暧昧却又感人至深的电影文本是个不折不扣的奇迹。
二、 手指飞舞,写下记录,继续向前,虔诚或者睿智都无法诱使它划去任何一行,即使是眼泪也无法冲洗掉任何一个字。——《十二只猴子》中的诗句
表面看去,《十二只猴子》讲的是时间旅行,我们就暂且把它当作一部关于时间旅行的科幻片来看。詹姆斯·科尔从未来回到现在,目的是采集50年前毁灭了大半个人类的病毒样本,并确认病毒是从哪里开始传播的。需要注意的是,科尔并不是回来拯救人类的好莱坞式英雄:他只能观察历史,但不能改变历史。这是影片的理论基础,也是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的影片之处。影片的海报上清楚的写着:“未来就是历史”(The future is history)。对于1996年的人们来说,人类毁灭还是未来;但对来自未来的科尔而言,这已经是历史了,而历史是不能改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5年的“未来”乃是科尔的“历史”,所谓“未来就是历史”便是此意。科尔本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精神病院中,他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医生们:“拯救你?我怎么拯救你?这已经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
然而在影片末尾,当他发现散播病毒的真凶后,却忘记了历史是不能改变的,如果他真能将病毒散播者击毙,岂不是改变了历史么?但是,他注定不能成为拯救人类的英雄,因为人类已经被毁灭了,无从拯救。科尔想改变历史,却在不知不觉中沿着历史为他设定的命运轨迹前进----而他的死,其实也正是这历史的一部分。希腊神话中的忒修斯被神谕判定会弑父,他的父亲恐惧中逃到一个偏远的小岛上,却不料在观看当地的竞技时被恰好参赛的忒修斯失手扔出铁饼砸死。俄迪浦斯王从小便因弑父娶母的神谕而背井离乡,最终还是在命运的牵引下回到故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应验了神谕。科尔之死带有浓厚的古希腊悲剧色彩:无论悲剧中的英雄是主动(如科尔)还是被动(如忒修斯之父),亦或无意识(如俄迪浦斯),命运之轮都将一如既往的将他们碾得粉碎。
无独有偶,影片中借蕾莉博士之口提到了卡桑德拉,希腊神话中的女先知,她能预言未来,却无法改变未来,因为人们将她的预言当作疯话置之不理。科尔实在是卡桑德拉与俄迪浦斯的结合,他能预言未来,却如卡桑德拉般被视为疯子;他想改变未来,却如俄迪浦斯般成为命运的玩偶。对科尔来说,“历史”便是希腊神话中的命运,挣脱不了的。历史便是历史,白纸黑字已经写下;而正如影片开头那个诗人所说的:“你所有的虔诚和智慧都不会使它有一丝挽回,你所有的眼泪都不会让它有一点改变”。所以,无论是虔诚还是智慧,还是蕾莉伤心的眼泪,都不能改变这一切。正因为如此,《十二只猴子》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而《终结者2》只是一个浅薄的童话而已。在《终结者2》中,超级计算机的雏形被来自未来的机器人毁掉,未来被彻底改变了。那么原先那个暗无天日的未来会怎样呢?在一瞬间阳光普照,亦或整个烟消云散?
导演特瑞·吉列姆的神话情结与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他早年是轰动一时的系列喜剧片《巨蟒》(Monty Python)的动画指导,而《巨蟒》的拿手戏便是以现代意识来解构大家熟悉的神话故事。例如《巨蟒和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调侃亚瑟王与圆桌武士的神话,《巨蟒在布莱恩的生活》(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则将圣经里耶酥的故事加以戏仿,结果在英国因遭宗教组织的抵制而被禁演。以吉列姆本人而言,他成为导演后的成名作《时间强盗》和而后的《吹牛男爵的冒险生活》(The Adventures of Baron Munchausen)都是纯粹的神话题材,而到了《渔王》一片,已然将神话故事不着痕迹的融入剧情,并探讨了神话与现实生活的同构性。《十二只猴子》比以上诸片更进一步,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虽然全片只借蕾莉之口提到过一次卡桑德拉,除此以外与希腊神话看似毫无牵连,但是无论情节,人物还是气氛都象足了经典的希腊悲剧,俨然一部索福克勒斯的大作。我第一次看此片时并没有觉察到,但到了第二、第三次,看到关键处却每每想起《俄迪浦斯王》和《美狄亚》。遍观当代影片,恐怕只有安哲洛普罗斯《尤利西斯的凝视》一片可与之等量齐观。吉列姆能借最现代的时间旅行来表现最古典的“悲壮”之美学境界,不由人不由衷叹服。
然而时间旅行的奥妙还不止于此,“未来就是历史” 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假如我们任意截取科尔被杀前的一个时间横断面,那么,对此时的科尔来说,他被杀这一事件到底是未来还是历史呢?答案是:既是未来,也是历史!一方面,科尔此时还没有被杀,因此这无疑是他的未来;另一方面,他6岁时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6岁时发生的事又应该是历史才对。既然自己的未来已是历史,我们不禁要怀疑到底是否存在所谓的自由意志?这恐怕也是时间旅行不得不面对的悖论:难道参与时间旅行者都是失去自由意志的傀儡?所以当科尔绝望的说:“我希望未来是未知的”时,我几乎能嗅到其中的酸楚。
当然,这些问题影片并没有作出满意的回答;事实上,它只是提出问题,而根本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正如我们将谈到的,看似复杂的时间旅行仅仅是冰山的顶端,海面下的一切将随着对影片的反复观看而逐一显现。
三、宗谱学真正的作用在于为那些不连贯的,不可靠的知识提供根据,从而反驳那些以真知和所谓组成科学及其对象的主观的想法的名义来过滤、整理、组织他们的统一的理论体的声称。——米歇尔·福柯《权利与知识:福柯访问及著作选集》
如果《十二只猴子》仅仅停留在对个人命运的感伤上,它无疑还是一部优美动人的电影,但绝不能让我如此疯狂的顶礼膜拜。与以往同类题材的影片,如《终结者》系列,《回到未来》系列等相比,《十二只猴子》的编导无疑具有更为敏锐的哲学嗅觉。
从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者往往都重“共时”(synchronical)而轻“历时”(diachronical),对他们来说任何一个系统都是时间的函数,只有将时间钉死才能放心地探讨该系统的内部结构以及由“差异”所产生的意义。而一旦放开时间这个变量,整个系统就会乱了套。用术语说来,就是所谓的“时序倒错”(anachrony)。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所谓“意义”,“真理”都只是由位于某个时间断面的系统发出的价值。正因为如此,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根本上动摇了相信科学真理,相信社会进步的启蒙主义理念。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是沿索绪尔的思路从系统内部解构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个思路,通过时序倒错的手法将不同时间的系统元素拼贴到一起,同样可以达到解构的目的。而时间旅行就是这样一柄能划穿真理之幕的利刃,它使我们意识到,并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真理,一旦脱离了当下的社会系统,很多“真理”都会显得滑稽可笑。事实上,“巨蟒”系列喜剧的卖点就在于此:让一群现代人穿上古代服装去演绎古代的故事,再庄严神圣的话语在其插科打混的伦敦脏话中都消弥于无形之中了。《十二只猴子》的编导显然是意识到了时间维度对真理的解构作用的。听听布拉德·皮特扮演的杰弗莱怎么说:“以细菌为例,18世纪时它还完全不为人所知!没人想象得到这样的东西——总之没有正常人想得到。”
导演是不是在暗示细菌,或者说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呢?没那么简单。一方面,杰弗莱只是指出,对18世纪的人们来说,细菌是不存在的;而对于我们20世纪的人来说,无疑细菌又是存在的。那么是谁掌握了真理?我们掌握了我们的真理,他们掌握了他们的真理,因为并不存在脱离时代的真理。如福柯所言,我们能掌握的只是一些当下的,松散的,不具普遍性的知识。而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杰弗莱是以疯子的形象出现在片中的,他口中的话又有多大的可信度?这就是导演的狡猾之处。但是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又会发现“疯狂”这一概念在片中同样遭到了无情的解构(见下节)。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福柯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科学史学家冈奎莱姆(Canguilhem),他开拓性的思想对福柯影响甚巨。冈奎莱姆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科学史上“真”与“伪”的界限之所以处于不停的变动中,是因为人们总是从当下的科学认识出发来书写历史。一旦当下的知识发生变动,科学史便得重新书写。换句话说,便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源自克罗奇语:“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编者按);如果把历史放到历史本身的框架里去理解,那么细菌在18世纪又何曾存在过呢? 一百年前看似坚如磐石的科学真理,如今看来却是破绽百出;同样的道理,假如我们从一百年后看现在的科学知识,何尝又不是破绽百出呢?虽然我们只能从现在回望过去,所幸还有幻想的翅膀带我们离开地面,让我们得以俯视因“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无法看到的种种地貌。时间旅行无疑就是这对代达罗斯之翼,使人们能够通过幻想获得解放。
深具艺术气质的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曾区分过纯粹的幻想与来源于生活经验的艺术再现。幻想所具有的超脱魅力是普通的临摹现实之作不能比拟的。如同在塔科夫斯基的《安德烈·鲁布廖夫》和《镜子》中反复出现的热气球,带有幻想色彩的艺术是所有为重力束缚者的福音。在瞬间的飞行中我们暂时失去了历史的重力、意义的重力和道德的重力,并且籍此首次意识到“重力”的存在。让·鲍德里亚在《末日的幻象》中更进一步指出,如果飞翔的速度超过第一宇宙速度,我们就会摆脱重力的束缚而进入太空,进入真正的虚无。在鲍德里亚看来,我们身处的现实已经提供了这个危险的加速度,而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否则,如何解释作为幻想之极致的科幻文学在当代的流行?我们还有对幻想的渴望足以证明“地域”与“地图”还没有合而为一。
而幻想文学,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无论是《十二只猴子》中的时间旅行,《基地》里的心灵历史学,亦或是《让我流泪,警察说》里能使时空变幻的毒品,它们提供的不是对科学技术的前瞻,而毋宁是一种反思现实的维度。
四、你知道什么是反常吗?反常就是“多数定律”。——《十二只猴子》中杰弗莱·曼森的台词
受冈奎莱姆《常态与病态》一书的启发,福柯写出了《疯癫与文明》。在福柯看来,理智与疯狂之间并没有一条永恒不变的界限,相反,这条界限随时代的变迁而偏移不定。在1600年以前,欧洲还没有精神病院,疯子们自由的在大地上游荡----那时作为社会的“他者”而被排斥的是麻疯病人。尼德兰画家波希(Hieronymous Bosch)的名画《愚人船》便是其最好的写照。巧合得很,虽然《十二只猴子》的导演特瑞·吉列姆从未承认看过福柯的著作,但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到,他的电影在构图上深受波希、老布鲁盖尔(Peter Breugel the Elder)和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的启发。我们只能凭推测来想象波希画中那些古怪痴迷的疯人形象到底对吉列姆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疯狂”作为一个主题在他的电影中反复出现则是不争的事实。由《巴西》到《渔王》再到《十二只猴子》,吉列姆对疯狂的描划愈来愈具穿透力,而《十二只猴子》几乎可以作为《疯癫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的脚注了。
来自未来的詹姆斯·科尔为什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其一,他没有任何证件证明其身份;其二,他口口声声说世界会在1996年毁灭。换言之,科尔的“症状”并非生理性的,而在于其与现实秩序的抵触。精神病院乃是维持社会合理化(justification/rationalization)的一条支柱,是所有远离社会理性内核之他者的归宿。“精神病人”往往是新时代里的女巫和卡桑德拉,想想梵·高、尼采、荷尔德林、克莱斯特、海子,乃至贞德……而如片中蕾莉博士所说:“我们所深信不疑的是现在被当作真理接受的东西,不是吗,欧文?精神病学——它的最新的信仰,就象牧师一样——我们判断对与错,反常与正常。”
或许比《十二只猴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阿根廷幻想影片《面向西南方的人》:一位睿智的外星人来到地球,竟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作为一门科学的精神病学试图将一切异象都加以合理化,纳入理性的疆域,于是便有了蕾莉所谓的“卡桑德拉情结”(Cassandra Complex)。在蕾莉煞有介事的将科尔的“症状”加以归纳梳理,并安上一个机智的标签的同时(明显是对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Oedepus Compus)和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的讽刺),作为个体的科尔已然如某纲某目的昆虫般被灰色的科学话语所吞没了。
不要以为我们看到的仅仅是电影。电影不过是一面银色的镜子,镜中的人或许就是我们自己。吉列姆因《巴西》一片被很多人称为银幕上的卡夫卡和奥威尔,然而《巴西》的开头说什么?“二十世纪某地”。他拍摄的不是未来,而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有着我们这时代烙印的“或然世界”(alternate world)。《巴西》如是,《十二只猴子》亦如是。不信你打开google,输入关键词“精神病院”,一连串如“一法官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变迫害工具”的字符便应声而出,触目惊心。最有意思的是一篇名为《精神病院随想》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实习的医学院学生,其最大的感想便是“对精神病的诊断,到目前尚没有客观的标准”。真是黑色幽默到了极点。
但如果这就是我们对电影的解读,那无疑又中了导演的圈套。《十二只猴子》是一部最彻底的反意识形态的影片。所谓意识形态,简而言之就是两分法,如迫害/反迫害,疯狂/理智,未来/现在,诸如此类。而《十二只猴子》更象是新历史主义学者格林费尔德(Greenfield)笔下那幅变幻莫测的画,时而是道貌岸然的贵族画像,时而是阴森森的骷髅头像,差别只取决于不同的视角。
布拉德·皮特扮演的杰弗莱是片中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他是如此的魅力非凡,以致后来皮特在《斗阵俱乐部》中几乎全盘复制了自己在《十二只猴子》里的表演。杰弗莱的形象拒绝一切意识形态化的分类:谁能说清他倒底是思想者还是行动者,是疯子还是先知?他更象一个古典时代的疯子----如福柯所言,那时候的疯子们不但没有失语,反而被人们视为真理和智慧的象征。他们是政治体制的无畏批评者,是“凤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舆,是第欧根尼的精神继承者。可是不幸生在二十世纪末的杰弗莱只能在精神病院里发表他的演说,即使他深具批判精神,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反对流行文化和本质主义。
五、这是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我发现自己在另一个星球之上,奥格星……尽管每个迹象都充分表明那是真实的:我能感觉,能呼吸,能听到;然而,尽管奥格星的经历确实是我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之所以精神错乱是因为我正在逃避一些不知名的困扰我的生活的现实,朋友,你是否也精神错乱呢?——《十二只猴子》中TJ·华盛顿的台词
詹姆斯·科尔究竟是不是疯子?这个问题,恐怕比“杰弗莱是不是疯子”还难回答。虽然我们想当然的认为他是个来自未来的正常人,但是不要忘了,所有的依据都来自我们正在观看的这个出自科尔视角的电影文本。有没有可能蕾莉博士说的都是真的,真有所谓的“卡桑德拉综合症”,而什么时间旅行,世界毁灭都只存在于一个疯子混乱的脑子里呢?如果是这样,我们从头到尾看到的一切其实只是一个伯克莱主义的“世界尽头”而已。事实上,这种可能不但存在,而且导演还在处处暗示,科尔在“未来世界”的所有经历都是“现实”在其头脑中的扭曲反映。我在片中找出了不下十处这种“幻想”与“现实”的平行关系,若说都是巧合,未免太小瞧导演的用心了,下面是影片中“未来——过去”的平行关系:
科尔在地面上搜集标本时看到一头熊——在飞机场看到一幅熊的巨型壁画;
科尔还看到了一头狮子——去飞机场时看到一头狮子塑像;
送科尔回到过去的发光的时间机器——精神病院里的一台发光的CAT机器;
到地面搜集标本之前的消毒沐浴——精神病院里的消毒沐浴;
在地面上穿的类似雨衣的服装——精神病院里为防止科尔伤人而穿上的类似雨衣的“紧身夹克”;
地面上搜集的蜘蛛标本——精神病院里吞下的蜘蛛;
在地面上进入的一个废弃教堂——飞机场的百货商场(实际上就是那个教堂的“未来”);
掌权的科学家们——精神病院审查科尔的医生们(在人数和性别比例上与前者都完全相同);
下监狱里征求“志愿者”的广播——飞机场征求“志愿者”的广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