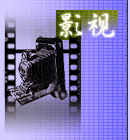编者按:玛丽亚
我可爱的玛丽亚
我身上很小的细胞,甚至比细胞更小的东西……
都在慢慢的死亡……
玛丽亚,我不再是我了…… |
|
一
东京。
气温最低的一天。
夜。
玛丽亚刚从夜总会出来,明天早上她还得到区公所上班,脚步有些踉跄,神情有点疲惫,手里那支香烟火光一闪一灭。就是那样的夜里,玛丽亚遇见一个男人,他刚刚出了车祸,后来告诉她自己失忆了。这个叫士郎的男人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的过去,他只是不想再当钢琴家,他只是不想再过空虚的生活。
士郎有一张温柔的脸,有一双温柔的眼,笑起来的时候比太阳神还要光彩。于是玛丽亚被打动了,她收留这个决意要斩断过去的男子,将心中的绝望暂掩埋。士郎抛弃妻子与荣耀,甘心为玛丽亚在夜总会弹琴,某一天他认为自己需要彻底的绝裂,于是当着妻子的面用碎酒瓶扎断了自己手上的神经。士郎会后悔吧?
玛丽亚身上的背负于是又重了,后来无论士郎堕落到何种地步,带给她多大的伤害;无论生活的路有多艰辛,前程多迷茫,玛丽亚总是对士郎不离不弃。这两个人,爱对方多一点,受到的折磨就多一点,离对方远一点,煎熬就更深一点。神拨弄着手中的命运丝线,嘲笑士郎的幼稚和玛丽亚的执着,这就是要自尊的男人吧?昔日光风的音乐家沦落到门成天文馆的收票员,这就是痴情的女人吧?甘愿为自己买下巨额保险,然后穿越东京街头打算撞车自杀。
二
我不知道这种极端的恋爱方式有何依据,反正在野岛伸司的作品中,总归会出现一个毫无目的,只管破坏的变态者。留美这次扮演了蛇蝎美人的角色,引诱士郎,找人去给玛丽亚破相,企图用这种方式满足扭曲的快感。然而开始的时候,野岛是那么温情地请求观者放心,因为玛丽亚逃脱了被毁容的噩运,也保住了腹中的胎儿;士郎拒绝了留美的诱惑,回到玛丽亚身边,他甚至没有听到玛丽亚的解释就相信她了。
可是短暂的和谐之后,野岛还是戏弄了我们的神经,他将整个故事拖向更深幽的谷底,甚至没有给这对情人重头再来的机会。留美倒底还是用毒品制服了士郎,将他那行尸走肉的躯体留在身边,玛丽亚的孩子还是死了,是士郎亲手所弑,他眼看心爱的女人用抽水马桶冲掉了整整一包海洛因后,终于发狂,狠狠踢中玛丽亚的腹部,这样的毁灭还不如,还不如先前……先前被旁人踩碎来得心安。
后来大概所有人都不忍心看玛丽亚的脸,那是一张被痛苦浸泡后仍不情愿服输的脸,拥有家财万贯的神矢征司就是被这样的脸征服的。他原本只是想和秘书玩个游戏,走进一家夜总会,看到玛丽亚穿着一身鲜红色,正奋力与另一个陪酒女郎打架,唇膏涂满了嘴边,秘书指着她说:“就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好了。”征司以为那是太容易赢的赌约,只恨他不是第一个遇见玛丽亚的男子。所以征司尽管可像神一般操纵他人的命运,却无法操纵玛丽亚与士郎的人生。
玛丽亚,我可爱的玛丽亚。
所有人都可以取笑。
唯独你,唯独你不能笑……
这是士郎最微妙的请求,他当时还不晓得自己会像冬季枯叶一般完全凋谢,他还以为手里握有玫瑰,到最后才发觉那只是一把刺人的荆棘。
三
士郎被玛丽亚带回公寓时已是满身狼籍,毒瘾与创伤几乎已将他撕裂,她将士郎绑在床上,用了很长的时间为他戒毒,给他治疗伤囗,玛丽亚那时真得像个圣母,在完成救赎使命。
痊愈后的士郎与玛丽亚分手,他们害怕再在一起,有些幸福可能是需要离别来完整的。就像深爱留美的痴呆男人,宁愿戳瞎自己的双眼,以避免看到她被硫酸腐蚀的脸孔,用残缺力求平等的相爱,士郎与玛丽安也是那样子的,非要给自己一些伤害,才可以给对方安慰。现实是一张锋利的齿轮,无论世人如何挣扎它依旧不依不饶地滚动运作,扎得人血痕累累也不会停休,所以士郎需要生命中的玛丽亚,而玛丽亚注定只能救赎,无法索取。
是谁说要离开现在的生活?结果便有人用一张木椅砸碎玻璃让他逃走。是谁说想要给玛丽亚幸福?有人就企图付出生命来交换。玛丽亚始终站在地狱边缘挡住士郎的去路,请他转回去继续生活。比如她已经坐上了飞往教堂的直升机,打算告别士郎与征司一起寻求安稳,当飞机越过所有人的头顶,高悬在空中的时候,玛丽亚一眼望见士郎,这个男人依旧还是眷恋的眼神,表情很无辜。
四
玛丽亚,亲爱的玛丽亚,她面容清丽,婚纱洁白,满面微笑得打开机舱的门,随后纵身一跃……
残酷吗?很残酷。
疯狂吗?也许。
这就是野岛伸司的浪漫,人人都爱红蔷薇,他只是不巧种出了白色的,于是等不及再浇灌出一朵来,只好割破手腕用血来染红它。那蔷薇摆在爱人的窗前,像玛丽亚的笑容。
玛丽亚
我亲爱的玛丽亚
我在茫茫人海中失去了方向
现在
就让我们这样一起生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