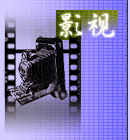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 编者按:张导的一部杰出电影,却被国内扼杀于摇篮中。 |
|
今天重看了张艺谋的《活着》。因为好几年前看过余华的原著,因此,在看的当会,不免要拿两者来进行一些比较。
在情节上,有着很大的出入。余华的原著里,福贵的家人一个接着一个死去,到了最后只有福贵一个人跟着一头老牛相依为命。而张艺谋的版本里面,虽然富贵的家人一个接着一个死去,但到了最后,至少还剩下他的老婆、女婿和孙子,一家人在一起乐意融融地吃饭。最后的福贵与孙子的对话也是令人深思的,表现了张艺谋对于生活确实是建立起了一个希望的坐标,并不像余华那样的绝望与虚无。
再而,人物的死去的原因也是张艺谋改变的最厉害的一个部分。在原著里,人物的死去,更多的是一些自然或者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死法,比如福贵的父亲,是在夜里蹲在田野里拉屎的时候悄悄离去的。而电影却是被福贵输掉了房产之后给气死的。有庆的死在原著是比较离奇恐怖的死,而在电影里却是一场车祸。凤霞的死虽都死于难产,但电影强调的是老医生因为多吃了包子而给噎着导致了凤霞的死,是一种很强的戏剧性的死亡。这里,我更喜欢的是原著里面每个人的各种死法,相对来说,没有太大的时代因素(当然跟时代也是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的)。余华确实很厉害,连各个人物的死都能写得如此浪漫而具有诗意,叫人敬佩。但张艺谋显然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把死亡跟时代连接成了一种必然的关系。这也造成了电影跟小说在主题上发生了质的变化。
小说的主题,其实上就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考。比如,人为什么活着?余华自己的解释就是“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并不为了其他东西而活着”。因此,虽然余华小说也是以中国上世纪40——70年代为背景,但并没有把时代背景作为造成福贵一家悲剧的来源去写, 而且是刻意淡化了时代的背景。有的只是一些诙谐的荒诞的还原,比如有庆建议怎么样去炼钢那一段,简直就是一个很荒诞的寓言。而到了张艺谋手里,他消解了余华所要表达的哲学沉思,而把重点放在了时代的烙印造成了人的苦难上,是一种对于当时社会的无情的批判和对于社会的反思,对于大跃进和文革,也都进行了一些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嘲笑,因此也是一个揭露社会的文本。就此来说,其实张艺谋就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他跟余华不一样,余华更关心的是人的生命个体,而张艺谋更关心的是社会的现实以及批判社会的决心和勇气,当然也正是这样,才使到张艺谋这部电影触动了中国某些脆弱的神经,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一部禁片。
最后,如果你问我觉得小说好些,还是电影更好,我可能会毫不犹疑回答:小说。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张艺谋的电影很烂,而是我更喜欢小说对于人物个体的关注。但张艺谋只是借用了余华小说的蓝本,其实内涵上完全是两回事。但我也同样喜欢这部电影,只为了张艺谋的勇气和决心。
最后说电影里面一个小段子:(靠记忆写下的,肯定跟电影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大跃进那会,全民大炼钢。镇长到福贵家去收铁的东西。
家珍:“镇长,这锅都砸了,我们以后还用什么吃饭啊?“
镇长:“以后都是共产主义了,都到公社去吃,鸡鸭鹅什么的,都能把你们撑死!”
镇长:“你们家还有没有铁的东西?”
福贵:“没有了!”
有庆:“爹,这还有!”(拖出了他爹的皮影箱和皮影,上面有铁丝和铁钉)
镇长:“福贵,你这觉悟就不如你儿子了,怎么铁钉铁线就不是铁了?这还能炼出两颗子弹来,兴许解放台湾到了最后,子弹打光了,就靠这俩颗子弹取得胜利了。”
福贵:“镇长,要不这样,我到工地给人唱戏,这皮影就不拆了好不?”
镇长:“也行。别的地方都是学生吹琴打鼓地给工人打气,我们就用你的皮影吧!都别拆了。”(镇长带人走了)
有庆:“爹,咱不解放台湾了?”
看到有庆的话的时候,我正在吃早饭。还好我忍住了,要不然,我的电脑可能现在就都是饭粒了~~呵呵~~
当然像这样的笑话里面还有很多,各位看客有兴趣就自己看去。当然在我们看来是个天大笑话,在当时那种民众的集体意识里面,这可是关系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是政治的、严肃的、伟大的。靠,看到这些我就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