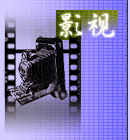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 编者按:一场《冰风暴》描述的是美国人处于于时代变更时的无措,脱不去的是东方美学表现手法的运用,这也是李安的特色。 |
|
 那部倍受赞誉的《理智与情感》,李安作为导演的功劳被作为该片编剧与主演的爱玛汤普逊遮掩了,人们把影片的成功更多地归之于汤普逊的编剧才华。在执导了这部《冰风暴》后,李安导演于影片居功至伟的作用才得到充分肯定,个中原因恐怕多少跟戏份很重的四位少年演员的出色表演有关,因为显而易见,没有导演对他们演出卓见成效的调教、驾驭,少不更事的小演员们不可能有如此丝丝入扣的卓越发挥,更别说很好地统一在影片鲜明的整体表演风格中了。 那部倍受赞誉的《理智与情感》,李安作为导演的功劳被作为该片编剧与主演的爱玛汤普逊遮掩了,人们把影片的成功更多地归之于汤普逊的编剧才华。在执导了这部《冰风暴》后,李安导演于影片居功至伟的作用才得到充分肯定,个中原因恐怕多少跟戏份很重的四位少年演员的出色表演有关,因为显而易见,没有导演对他们演出卓见成效的调教、驾驭,少不更事的小演员们不可能有如此丝丝入扣的卓越发挥,更别说很好地统一在影片鲜明的整体表演风格中了。
透过指导演员演绎的角色,李安在影片里塑造了异乎寻常的两个美国家庭,两辈美国人。说它(他)们异乎寻常是指主流美国电影中那个温馨、牢固、神圣的家庭,以及家庭中那些有力、正义、智性的父母,那些无邪、活泼、可爱的儿女,在《冰风暴》中见不到了,相反,是上述形容词的反义词可以形容李安“绘制”在银幕上的这一个“家与人”。事实上,许多人为《冰风暴》真实反映了七十年代初美国家庭的精神面貌深深慑服了。大家知道,六、七十年代是西方社会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道德观念,以及政治理念等等经历剧烈震荡的时期,在许多美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里,我们曾经领略过发生在那个社会时代背景中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领域种种乌七八糟的事,《冰风暴》里的两家人我们在小说世界里似曾相识(影片本身改编自一部享负盛名的小说)。虽然表现那个年代的美国家庭的影片并非仅见,然而,达到了诸多美国作家对之的表现深度,并且极富一种我们在阅读美国小说大师们描述那个年代的人和事时特有的韵味的,电影《冰风暴》可谓绝无仅有。触及了美国家庭问题的两部奥斯卡获奖片《克莱默夫妇》与《阿甘正传》我们印象深刻。前者,克莱默夫人离家出走作为对沉闷的婚姻生活的反抗,但是,她的行动在《冰风暴》中的伊莲娜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因为伊莲娜明白,走出婚姻家庭,于她倍受困扰的精神世界无补。虽然克莱默夫人毁掉了自己的婚姻生活,但克莱默夫人的形象非但无损,甚或被罩上了精神升华的光环,因为通过出走和离异,她的理性、强大和自我再生能力得到了重申、肯定。这是典型的西方思想方式。至于《阿甘正传》,那是用自嘲的笔调绘制的、映衬在美国社会历史大背景中的一名美国人传奇经历的连环漫画,虽然影片是阿甘的故事,但其历史时代场景是被着力凸现的,尽管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呈现。它与《冰风暴》不同,后者的历史性标识被缩减为几次尼克松为水门事件狡辩的电视画面,影片镜头全部聚焦于两个美国家庭,叙述两个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影片创作者的全部兴趣,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被一概删略了。影片继承了少数美国电影和不少美国文学作品中对家庭问题的反思、批判精神。所不同的是,这次自我批判是由一个华人来实现的。
那么《冰风暴》暴露的美国家庭的景像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影片中家庭内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成问题的,不管是夫妻、兄妹、兄弟,还是父子、母子,以至邻里、朋友,传统上家庭赖以建立,并且所维系着的那些关系,如今锈迹斑斑,问题重重。家庭象是茧,而人是其中的蛹,家之于人是人慵懒困顿于其中,既无计逃避,也懒得离弃的东西。人与人互相达不到对方,仿佛隔着某种无形的屏障,人们在相互打交道中充斥着挫败感。我们看到:作为夫妻,本恩与伊莲娜貌合神离,影片间中透露,俩人正为离婚问题困扰着;本恩与儿女保罗、温蒂之间,弥漫着对对方的困惑不解,尤其是对于半大不小的女儿温蒂蛮撞的个性,父亲本恩常常只得恼羞成怒;在保罗、里百特斯与弗朗西斯的关系中,保罗要俘获里百特斯就得抗击来自“性强者”弗朗西斯的威胁。而在占母、詹妮、桑迪、米奇一家里,妻子在与人通奸,母子、父子常常因为对方的莫名举止而错愕,就连兄弟之间也有问题——温蒂周旋于俩兄弟之间。
勿庸置疑,性在影片中,在家庭内外人与人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在影片里贯穿了两辈人(人们不无道理地把六、七十年代概称为西方性开放的年代)。性,它是人们因为有问题而寻求的一种解决方式呢,还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性而引起的?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个问题不好解答,可以肯定的是,影片显然在告诉你,纵欲——性解决方式,无论是通奸以至换妻,还是少年人那份朦胧但顽强早熟的性欲,都不是解决我们人在家庭生活中遭遇到的精神困境的方法。
显然,影片在世界观上本来可以是悲观的,影片的素材具备了一部悲观厌世的现代主义作品的要素,但是相反,影片令人惊叹的正是,它虽然尖锐地揭露了现代美国家庭中最荒唐的一面,令人震惊,但影片中的人物却没有受到贬低,而是始终保持着一种人的尊严感,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认为,这份尊严感首先来源于人之所以为人,敢于自暴丑行的勇气,这是人类理性精神的体现;其次,所谓的丑行是人类必然有缺陷的必然体现,是人们冲破茧缚,渴望生活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是人自然、合理的行径。詹妮与本恩的通奸及之后中断,伊莲娜与占母在“钥匙派对”上的亲密尝试,温蒂与桑迪、米奇兄弟对性奥妙的探索,本恩与伊莲娜危在旦夕的婚姻生活背后、两颗心灵的涟漪以至动荡,所有此类道德不伦都因为它们发乎人类真性情,而能够在电影观众面前体面地进行。一方面我们说影片中的丑行无损于当事人的尊严感来自西方精神中的自我批判传统,一种理性辩证意识的胜利,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种成功的自我批判是由一名东方导演来完成的。
在影片已有好的剧本基础和演职员的共同努力下,李安把东方主义精神注入了影片——不带先入之见,贴近生活和人物,完全聚焦于人及其生活原态,对人的状况,特别是人的精神状况倾注关怀;摈弃西方思维一定要从根源上探究,依靠建立深度模式,流于抽象,充斥隐喻和象征的间离式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方式。在李安的批判方式中,一切问题始于细处止于细处,你看到和听到的就是问题的全部。东方主义的要义在这里体现了出来:直观性、零散性、非根源性。
东方主义还体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保持距离。距离美是东方美学一个重要的概念,虽然这一美学原则在东方电影作品里很少被自觉贯彻(东方电影一古脑儿投入了好莱坞的怀抱),但它贯彻在绘画、诗歌、小说等多种经典东方艺术的艺术精神里。正如西方人眼中羞涩、含蓄的东方人一样,祟尚距离产生美是西方对东方艺术的印象,是东方艺术重要的美学贡献。李安电影最重要的美学意义就是继承和发扬光大了这一东方美学思想,这使他称著于西方,并且区别于陈凯歌、张艺谋等中国导演。
那么李安的东方主义如何具体体现在影片中呢?
1.对角色内在与外在,事情前因后果,人与人的关系不妄加定断,让其保持浑然一体,不可拆解的状态,令人物存有神秘性,正如现实生经验里,我们既不真正了解别人,也不真正了解自己。我们对影片中很多人的行为感到诧异不解:保罗对里百特斯的追求是一种意图和方式都不明朗的追求;温蒂喜欢的到底是桑迪还是米奇;米奇为什么在洗手间嚷了起来;伊莲娜与牧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桑迪之死与影片的深层意旨到底有怎样的关系,等等。
2.无中心视点,故事在两个家庭两代人内部散漫编排、均匀对称、复式特征的整体结构。对两个家庭里八个人物的叙述份量,虽然不能说是平均的,但显然影片中没有一个人物被赋予了压倒别人的优越视点,每个人物都从自己的角度看到了这个世界,而且表达了他(她)的世界观。另外,每个问题都是成对提出的,对应或者对称。例如,有本恩与詹妮的通奸,就有占母与伊莲娜的“性感邂逅”;保罗与弗朗西斯都在追求里百特斯;父母辈的性问题对应于子女辈的性问题;桑迪与米奇一起之于温蒂。所有这些,在我看来,与东方艺术有着似非而是的关联。
只有批判才有希望,同时,人与人之间,交流是克服绝望的根本渠道。我们看到,剧中人一方面是交流阻断的,而一方面也是渴望交流的:保罗与利百特斯、桑迪与米奇、保罗与家庭父母……
米奇在冰风暴之夜(也是荒唐透顶的“钥匙派对”之夜)的死,把影片的感染力推向高潮,如同一根弦被一点一点拧紧,骤然间嘣地一声绷断,米奇之死具有感人肺腑,令人不胜唏嘘的悲剧艺术效果。我们说,米奇是一场冰风暴的偶然性的受害者,也是人的一次精神劫难的必然报应。同时,他的死有着象征意味——旧的死了,新的能够开始吗?在新的一天的黎明,人们都带着极度的疲惫神情,在前一夜,每个人都发生了、经历了重大事情。新的一天开始,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
保罗出现在车厢的出口,昨晚,他毅然离开了没有防御能力的里百特斯,冒着冰风暴赶回家里。他是影片中唯一一个对性说了“不”的人。在车站上迎接他的是全体家人,这似乎寓意着,希望只能重新回到家庭中去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