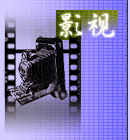雨天。阑珊中读着塞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前晚被喧杂猛烈的电子乐带动起来的激情,已渐渐远逝。此刻,闲散而有点惘然。窗外,春寒料峭,细雨迷蒙。亢奋与低迷似乎总是呼应、相伴,有如四季循环,有如生与死?
塞弗尔特在春寒料峭的三月去维榭赫拉德墓园,孤零零一个人凭吊离去的诗人老友,却意外地在那里遇上年轻陌生的姑娘,她拿着诗人的诗集,在朋友墓前献花,塞弗尔特不禁突突心跳,“一种温柔的、既古老又甜蜜的情思轻轻地拂到我的脸上。怎样的忧伤啊!”他写道。
这种体验,只有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寂寥日子后,记忆的游丝从岁月深处被唤醒时才能产生。这是何等细致、忧伤的情怀!
此时,有人招呼我去看导演版《无穷动》。为什么不呢?我对自己说。于是,我吆喝了一些朋友同去。
宁瀛过去的“北京三部曲”虽没看过,但听说口碑还不错。据较为八卦的朋友说,《无穷动》已在北京引起很大争议。此次,宁瀛亲自携片来上海。八卦消息恰到好处地点燃我的观看兴趣。
在一个四合院里,四个临近更年期的女人在谈论男人与性。话题起因是因为洪晃(恕我以扮演者的名字直接代替角色名字,此片没有编剧,导演让她们随意发挥,正是要展露她们内在的真实性)发现她的女友中有人与她的男人有私情。洪晃邀请她们到家中做客,想探明这人究竟是谁。最后,当洪晃接到电话,被告知她的男人被车撞死了时,其中一个女友嚎啕大哭,另一个人发疯。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不仅影片中没有男性角色(而我以为真正的主角恰是没出场的男人),四个女人还以极为张狂的言语嘲弄、抨击男性,已到了疯狂的边缘。她们以猥亵、轻蔑、戏谑的口吻谈论男人与性,却掩盖不住对男人的性趣和倚赖;而又在贬低男人的同时不忘自我炫耀。
我猜想,宁瀛是想拍一部涉及女性内心的电影,一种具有精神意味的带有探索性的影片。她通过四个女人的一天生活来展示她们人生的片断和经历。从影片中可以看出,四个女人都受到过某种程度的伤害,否则就不会显得如此乖戾、变态,而这种伤害应该不全是来自男人,更多地是来自社会——特定时期的某种时代的烙印。影片中有个细节极富含义,印证了是过去年代在她们身上留下印痕旧戳的看法:打断她们谈话的是一只鸟飞进了阁楼,她们去阁楼驱赶鸟,结果发现阁楼上存有许多旧物,比如:线装书、毛主席像章、一些革命时期的胶木老唱片等。问题是为什么她们最后把自己的失意、磨难都归咎于男人?将美好的男女关系定义为战争的双方?
坦率而言,影片的某些细节有着岁月淡淡的留影;镜头运用也较为精致,使影像含有飘忽的意味;刘索拉的配乐也有一定的特色,惶惑中带着若有所失的味道,使影片具有难能可贵的悠悠岁月的格调。有人说,这部影片有纪录片的影子,而我更觉得有侯麦的情致——那种通过在客厅里随意聊天呈现出特定人群的特定情怀。甚至作为男性,我也并不十分讨厌其中流露出的强悍女权色彩。只是影片缺乏内省、知性的元素,四个女人像是被无法制止的车轮在永远地滚动。
与其说,这部影片讲述了中年女性的精神失落;不如说,影片展现了她们过渡扩张的欲望;或者说,她们的失落正是由无度的扩张造成的。失落与扩张纠缠在一起,从而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然而遗憾的是,影片中的女人并不明白这一点。
由章含之女士扮演的女佣张妈,是此片中演得较好的角色。也因为有了张妈这一角色,才使影片稍稍有了一点疏离感:她冷眼旁观那拨女人在“抓狂”,带有一丝无奈和宽容——一种只有当下时代才可能有的姿态。因此,我也以如此态度看待此片。
……夜晚,当我将上述观感写下后,才因影片(由演员而不是由内容)引起的不适感驱散。雨,仍在绵密地下着。窗外一片寂静。冷风带来了一丝清凉的气息。我静静地谛听雨滴由一片树叶滴落到下一片树叶传来的空灵的声音,对我来说,这音韵似乎含有某种前奏曲的意味,令我陷落了更寂静的境地,令我想起了早年曾写过的一首关于萧邦的十四行诗——也是在这样湿润的空气里。我打开书籍,重新延续下午被中断的阅读。我看见塞弗尔特在书中另一处写道:“最大的战争爆发了。诗人们除了沉默之外别无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