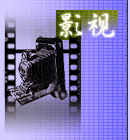大提琴的琴声竟是如此的激昂澎湃,犹如山体崩塌,洪水急泻般,硬生生的冲入我的记忆中;哀恸、紧绷的琴声鲁莽而直白的击中我的肺腑,在刹那间,我的心仿佛被掏空了一样,轻飘飘的,抓不住一丝跳动的痕迹。镜头随着大提琴的伴奏,在漆黑、蜿蜒的隧道中急速的向前行驶着,直到在那抹亮光的尽头,一副没有了灵魂的身躯呆滞的走向镜头的延伸!
影片一开始,里奥.卡拉斯就为整部影片奠定了强烈而压抑,沉重而激情,炙热而痛苦的让人紧张的无法喘息的大基调,预示着爱情的来势汹汹,里奥.卡拉斯直言不讳的开始对他的爱情内心独白进行着最为深刻、有力的雕刻。
里奥.卡拉斯显然是一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他放弃了法国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而将镜头对准了新桥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从而决然的把影片角色的社会背景放在了社会的最底层,剔除掉了在人物背景里的属于物质的客观因素,似乎只能这样,才能表现出里奥.卡拉斯爱情的纯粹性,才能更加绝对、立体的呈现出男女主人公之间不带有任何杂质的烈焰般的情感。然而,里奥.卡拉斯似乎仍不满意自己所创造的这段苦情,他硬生生的让女主角的家庭背景与整个影片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进而,为影片的后续发展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影片社会背景的设定是整部电影的骨骼架构,那么,人物角色的临摹就应该是影片的肌肉,而里奥.卡拉斯正是使影片变的鲜活起来的血液。如何使影片的肌肉具有更强大的爆发力,里奥.卡拉斯更是不余余力的将人物推向了塑造的极限。男女主人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同时,亦为身体的残疾人士。这样两个处于社会最边缘的人物,因为里奥.卡拉斯的固执,因为里奥.卡拉斯的热情,因为里奥.卡拉斯苦其心志的精心营造,展开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惊世情。
米雪第一次见到亚历时,醉的不省人事的亚历醉倒在公路上,一辆高速行驶的轿车急速的亚历的脚踝上辗过,亚历依旧躺在那里,动也动,没有一丝声响,没有一丝呻吟。深夜到处是一片死寂,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一种幻觉,都只是一场了无痕迹的梦魇。那是米雪第一次见到亚历。那时的亚历只是一个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那时的亚历还不知情为何物,那时的亚历变成了跛子。而在影片中当米雪留书与亚历不告而别时,亚历绝望的举起了情人留下的唯一的一件东西,曾经是他们爱情的见证——手枪,此时的亚历已经有了家的感觉,此时的亚历还在为爱而痴狂,此时的亚历用手枪将自己的手打残。这一前一后的一跛一残,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称与行为上的统一,使影片的主题更为紧凑、层层递近、浑然一体。前者。亚历被动的被轿车辗过,如此切肤只痛没有让亚历有所知觉,而后者,当心爱的恋人离他而去时,亚历自觉的用手枪打伤自己的手,那决然的神情不难看出,当他保留那把枪时,心里早就有着强烈的不安与痛心疾首的决心。这一枪,让亚历将他那夭折的爱情永远的镌刻在他的伤口上,随着一声枪响,所有的一切包括亚历尘封在往昔岁月的无限追思中。这种从被动到自觉情感的复苏,正是里奥.卡拉斯镜头下表现最为魅惑人心、瑰丽的爱情魅力。
然而,里奥.卡拉斯是贪婪的,是唯美的,是不容许他的镜头下的爱情故事有丝毫瑕疵的。米雪因为情人大提琴手的离弃,而放弃了富裕的生活环境,宁愿过着自我放逐的流浪生活,已最为消极的态度去哀悼她逝去的爱情。甚至在流浪中,米雪都没有放弃寻找大提琴手的念头,虽然,在影片中米雪幻想自己用枪打破了大提琴手的头部,显的很残忍,但真正印证了那句老话“爱之深,恨之切”。痴情如米雪,在里奥.卡拉斯的狂热内心里,她又怎会不遇上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痴情者亚历。亚历第一次看米雪为他画的素描时,就深深爱上了米雪。甚至,深夜不惜涉险去家里找米雪的手稿。由此,有谁会不相信里奥.卡拉斯不是一个痴情快意的唯美主义者呢?这样的人物塑造怎会不具有爆炸力?里奥.卡拉斯几乎宿命的将这两个完美爱情的象征符号用他最华丽、最窒息的镜头语言浓缩的揉和在了仅有几毫米的胶片上。
影片至始至终都贯穿着亚历对米雪强烈而绝望的爱意。其中有一幕戏至今让我想起都无法平复心中的酸楚。米雪在老流浪汉汉斯的帮助下到画展中心去观看她向往已久的名画,烛光映衬下,米雪一如膜拜的抚摸着那一幅幅的美丽画面。而此时,痴情的亚历绝望的以为米雪已离弃了他而用酒瓶在他自己的身体施虐,以减轻那附着在他灵魂上的痛恻心扉,当米雪回到新桥之时,亚历兴奋的掩面而泣,米雪望着悲喜交加的亚历,想籍以自己的柔情与拥抱去抚慰亚历受伤的心灵时,可是固执的亚历不敢靠近,倔强的米雪牢牢的包住亚历,赫然发现亚历身上那仍旧还在滴血的一道道伤口布满了全身,亚历泣不成声,那身躯因为哭泣而在寒风中不停的颤抖,米雪几近无奈、无限悲伤的狠狠抱住亚历,仿佛要把亚历揉进自己的身体一般。我不知该怎样表达我的心情,只有一种心酸在心中不断的滋生,是的,是一种心酸,心酸的让人欲哭无泪。我不禁想起格非在“欲望的旗帜”中写到“认识你之前,我是寂寞的,认识你之后,我是孤独的”。里奥.卡拉斯竟然“残酷”如斯,他总是把情感之外的,灵魂之外的躯体当作垃圾一丢掉,似乎那是多余的,那是形而上学的,也许里奥.卡拉斯更是一个柏拉图的拥护者。
影片的结尾将整个爱情故事推向了高潮,同时里奥.卡拉斯也将乌托邦式的理想爱情表现到了极至。里奥.卡拉斯戏剧性的将笔锋一转,在诗一般的冬夜里爱情堆积成永恒的洁白,所有的骚动、不安、压抑、焦灼、痛苦、窒息随着那一片片的雪花在静谧的严冬深夜化成一滴滴晶莹剔透的水珠,汇集成涓涓细流,流向大海,流向远方,永远的远离了新桥。里奥.卡拉斯在结尾的神来之笔,使整个影片在意识立意上达到了高度统一,从而更能窥探出里奥.卡拉斯这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对完美爱情的执着向往,岂不快栽,美栽!
如果要用绘画来形容一部电影的话,那么“新桥恋人”显然是一幅色彩绚丽,浓墨重彩的油画。它的层层推进,重重叠加,使整个影片在里奥.卡拉斯张力十足的镜头前无处遁形。本片最大的两个亮点为,里奥.卡拉斯激情四处的导演和茱莉叶.比诺什细腻深邃的的表演,为此茱莉叶.比诺什还凭这个角色获得了当年(1992年)欧洲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在影片中那种几乎贯穿全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情怀把人们带入了熊熊燃烧的火焰中。与其说“新桥恋人”是一部成功的影像作品,我更加喜欢把它认为是里奥.卡拉斯爱情的内心独白。里奥.卡拉斯倔强的犹如一个孩子一般,肆无忌惮的把自己对爱情全部遐想放在了影片的每一个角落里,豪迈的挥洒自如,我行我素,让人不由自主的被他的热情所感染,浓浓的情怀扑面袭来,挡也挡不住。
就影片而言“新桥恋人”是我看过最为流畅,最为饱满的爱情影片,我不想去掩饰对它的喜爱,就好象里奥.卡拉斯从不隐藏他火一般的热情,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情理想主义者!也许正因为如此影片在过去了近十年后,依然获得了芝加歌影评家协会最佳外语片的提名。现在我们似乎还能够感受到影片中熊熊燃烧的爱情炙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