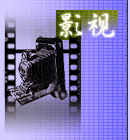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 编者按:更多人认识台湾女作家朱天文是因为侯孝贤的电影,而在电影与文学之间,到底她是一个怎样的朱天文呢?因为她是胡兰成的爱徒,因为她和侯孝贤、吴念真的铁三角,还是更多的其他使得这个女子显得那般不平凡呢? |
|
某种形式的文字,比如小说,改编成电影,要经历不同符号系统的转换和跨越。小说的叙述,在假想空间通过错综复杂的时间进行,有如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而电影,要在空间的流动中完成叙述。
文学之于电影,如同玛格丽特·杜拉之于阿仑·雷乃,朱天文吴念真之于侯孝贤。是干将与莫邪,是天雷地火。当年作家云集的法国塞纳河左岸,培育出了《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出现了用文学作电影游戏的阿仑·罗伯—格里叶。
爱森斯坦认为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特写描述法对格里菲斯的蒙太奇手法有直接影响。许多年来,希腊史诗、各国神话、莎翁戏剧、各国小说……都是电影虎视耽耽百看不厌的题材。
吹梦到西洲
侯孝贤电影始终的书写者、记录者,台湾女作家朱天文,最初淡入我们的视野,不是因为文学,而是侯孝贤的电影。如今,她的小说集《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散文集《花忆前身》,剧本集《悲情城市》都已花开大陆。才情在文字里,较之间接的影像,愈发精致迷离。
朱天文出生于1956年的台北——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原籍山东临沂。父亲朱西宁与台湾作家司马中原、段彩华被目为“虽乏武功倒有文治”的“军中三剑客”。母亲刘慕沙亦从事翻译工作。数十年来,朱西宁夫妇和天文、天心、天衣三个女儿共出版了70多本书,可谓“小说家族”。
父亲朱西宁于1998年辞世。朱天文在散文集《花忆前身》里用一张图片纪念他。父亲白发飘扬,独立暮草间的凝思凝固在黑白画面里。画面外是数枝花蕾,录像机上仰天长啸的白猫和绿眼熠熠的斑纹猫。
朱天文秉承家学渊源,神情自幼有不寻常之处。一张泛黄的图片里,三岁的朱天文短发微卷,鼓脸,圆眼睛和淡眉,嘟着嘴,白短衫和背带裤,露着白生生的胳膊和脚踝,昂首向天,一副清傲和任性模样。
朱天文高中开始写小说,十五、六岁即在文坛崭露头角,1978年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是年,大陆“第五代”导演们跨入北京电影学院朱辛庄校门。
大学毕业时的朱天文,装扮黑白分明,一时惊艳——绝非明艳,却无论如何让人眼前一亮。朱天文脸颊从容,蛾眉淡然,眼神清亮。那种笃定和任性,看不出她文章里所说的毕业时的不安。
没有如她的外文系同学漂泊海外或者商界,朱天文毕业后创办了《三三杂志》、《三三书坛》。老师胡兰成写信给她道:“三三命名好,字音清亮繁华,意义似有似无,以言三才、三复、三民主义亦可,以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亦可。王羲之兰亭修楔事,与日本之女儿节,皆在三月三日,思之尤为可喜也。”
朱天文和天心姐妹才情相当,各有千秋。天文细致温雅,偶有尖刻;天心关注时事,爽朗阔达。十几年来,两人屡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和时报文学奖,姐妹俩曾一举摘取图书三冠王的桂冠,名重文坛。美丽与才情,在文坛姊妹花身上同时绽放,也是赏心乐事。
至今不婚的朱天文,被评论家称为“可恋慕的美女作家”,被目为“继承了张爱玲半个世纪以来的绝响”。她坚韧地为笔下的芸芸众生寻找救赎……
上个世纪末的《亚洲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上,赫然写着:
第54名:《世纪末的华丽》。作者: 朱天文
误入藕花深处
朱天文因为《小毕的故事》,误入藕花深处,开始了与侯孝贤的合作。其后,与吴念真、侯孝贤合作编剧创作了诸多闻名影坛的台湾新电影,开辟了台湾的新电影时代。从此,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而不得返,与侯孝贤共事十余年,合作过十个剧本。
六十年代,琼瑶电影成为台湾电影史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第一波高峰。八十年代台湾新电影改编多部当代台湾小说,多为朱天文、王祯和、李昂、白先勇等人作品,是为台湾文学改编成电影的第二波高峰。创作者们苦心孤诣吸引观众回流,挽救台湾电影颓势。
朱天文改变了侯孝贤。她小说的叙述语言对侯孝贤电影叙述风格的成长深具启发作用。法国导演阿萨亚斯说朱天文对侯孝贤电影演进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使他朝着一种越来越果敢、现代的叙述语言迈进。
《小毕的故事》之前,侯孝贤的爱情喜剧片《儿子的大玩偶》之类大致上仍不脱叙述线主轴分明的好莱坞经典叙述。朱天文小说散文式枝节庞杂的叙述模式,鼓动侯孝贤发展一种反戏剧高潮、清淡散文式并扩张影像诗质的叙述语言。
侯孝贤影片《冬冬的假期》就完成了文字与影像的跨越。从朱天文《安安的假期》童年忆往式的乡愁,化为侯孝贤《冬冬的假期》土地凝视的超越体悟。侯孝贤以完整的个人风格诠释改写着原著,藉影像记录自己对台湾土地和人的情感。
侯孝贤旷达洒脱的长镜头,伴以朱天文中国古典文化深厚的细腻诗情,刚柔相济,疏密有致。偶尔吴念真的加入,侯孝贤的电影愈发显得理性与感性纠结相随,潇洒畅快。《悲情城市》有家国悲哀反省,也有素朴生计儿女情长,和东方情调。朱天文因而也有感慨无数。
《〈悲情城市〉十三问》里,朱天文追述编剧路途,“初时看书,忘路之远近,上溯到清末台湾五大家族……材料的丰富浩瀚把人诱入其中无法自拔……这个过程,我鲁钝才学到,编剧其实也是一种如何兼备理智和豪爽去割爱剪裁的过程”。
又说,“一切的开始从具象来,一切的尽头亦还原始具象。”再看《悲情城市》的剧本和电影,如同同父异母的兄弟——又何其不像,简直两样。
重温心神之后,朱天文在帮助侯孝贤寻出以往影片中不甚妥帖之处,作为对影像文本之后的文字书写。她说《童年往事》“还可以凝聚到内容里面,譬如像收音机播放金门炮战的消息这些做法,其实都太容易了,应该要渗在生活之中透出才更好。”这让我想起贾樟柯的《站台》,有些地方是生生别扭的,只是无法尽述,此处的理由,用在《站台》何其恰当。
朱天文是个性的,倔强的。侯孝贤电影中那些细腻曲折的心事显然出自她手。如同我们经常见到的那样,一个成绩优秀遵纪守法的乖女生与某离经叛道的淘气男生某日脾气相投,两个同样清高孤傲目高于顶,却必生出一段棒打不散的孽缘——只是,这是台湾电影的幸事,也可称电影史上的绝唱。
从此,朱天文不再能淡泊地“挥兹一觞,陶然自乐”,也不必孤寂地“清琴横床,浊酒半壶”。
此时的《千禧曼波之蔷薇的名字》在电影节上屡屡落败,也许是侯孝贤和朱天文的深秋来了。好好地冬眠一场,春天依然美丽。
舞低杨柳楼心月
有人说,朱天文堪称最刻意援引欧洲十九世纪末性别跨界与颓废的当代台湾作家。她用华丽张致的文字书写女性情欲。她的笔下出现了反爱情的倾向,爱情被调侃为幻想,其真实感不如欲望。她往往仍从好女孩/女人的视角出发,但对浪荡或出轨的坏女孩/女人则态度暧昧,而其好女孩/女人也异乎传统定义,表现出情欲上的自主性。
不是对官能世界的诱惑有着由衷的好奇,写不出那样的欲海浮世绘;不是对时间及回忆的虚惘有着切身的焦虑,写不出那样有惊梦意境的道德剧。游移于道德与颓废间,她的文字模棱周折,千回百转。
朱天文的早期作品如《小毕的故事》、《童年往事》等重于描述岁月悄移中人间温情,怅然惘然,冷峻犀利地剖析台北这个已被完全物化的现代都市,客观审视着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个性畸变,笔法苍凉练达。
《伊甸不再》《安安的假期》等小说创作于八十年代初,标志着朱天文小说风格的确立。《安安的假期》着笔于少年、青年的生活和情感世界,细腻探入他们的灵魂,笔调朴素淡然,气氛醇厚宁静,风景美丽如诗。
《伊甸不再》表达着朱天文小说纯净美丽之外凌厉泼辣的一面。有人评价道,“文字泼辣似男儿,小说的放胆利落,有时到令人咋舌的地步。”
《世纪末的华丽》与《荒人手记》里刻划出一种纵情难返的唯美耽溺、情欲衰疲与性别无政府。耽美的文字及颓靡的美感使两书成了台湾小说中阴性美学与世纪末颓废的经典之作。朱天文笔下的女性自恋而实际,内在强悍,充满自我意识。她们彷佛中了药瘾般沉湎于私密的情欲想象,却不会痴傻地投入没有胜算的爱情关系里——不知这是否朱天文自己的写照。
在一篇序言里,朱天文写道: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生活本身,那些广大在生活着的人们,总是令我非常惭愧。人,才是最大的奇迹和主题。
垂手明如玉
朱天文,非常台湾非常现代感的朱天文,是胡兰成的爱徒。
有一段时间胡兰成住朱家隔壁,教朱家姐妹熟读古书。朱天文忆道,“大家挑里面喜欢的篇章读,采莲采萎,又是一番气象。念到《西洲曲》,一句“垂手明如玉”,胡老师说:‘这是写的天文小姐哩’。真叫人高兴”。
父亲朱西宁与其时在美国的张爱玲书信往来,胡兰成也每每提起张爱玲的倔强和宽忍,少年朱天文已经有意识在模仿张爱玲。她说,“我在学张爱玲,学我以为的特立独行,不受规范。”
她也警戒自己有耽美的危险。可是这耽美的脾性会历久弥坚。1998年的戛纳电影节,《海上花》华美繁复的海报前,朱天文的笑容有一点凄惶。四十二岁的年纪,“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对于这样一个耽美的女子,是有些残酷的。
朱天文喜好浪漫唯美,也很物质,而且自恋丝丝缕缕。小说里朱天文写道,“女人自恋犹可爱,男人自恋无骨气”。还有,“世界绚烂她还来不及看,她立志奔赴前程不择手段。物质女郎,为什么不呢,拜物,拜金,青春绮貌,她好崇拜自己姣好的身体。”
她迷恋地用文字记述着自己与女伴去公园喝酸梅汤吃烤鱿鱼,去西门町看衣服鞋子吃老爷冰淇淋和棠梨。她爱看新娘装,可是并没有作新娘。她的文字也毫不掩饰对美丽女伴的倾慕。
朱天文承认自己逛街买衣饰的兴趣比买书大多了。“相信女子如我辈这皆有同感,衣服实在比什么都是女人的知己”。她素喜中式衣衫,丝滑闪亮的,桃红水绿如“桃花精”的,宽袍大袖的,蜡染的,斜襟盘扣旗袍领的……别有韵味。
《世纪末的华丽》中,女主人公是服装模特。朱天文用笔过足了美丽衣装瘾,而且描绘出文化意味。“印度的麝香黄。紫绸掀开是麝黄里,藏青布吹起一截桃红杉,翡翠织翻出石榴红。印度搏其神秘之淫,中国获其节制之淫,日本使一切定形下来得风格化之淫。”
性情刚烈固执的朱天文文字里无法掩饰些微的女权意识。她相信直觉和感性。“如果男人破坏了理论和制度会变成虚无主义,而女人再堕落也不会落到虚无主义,因为物质自身的存在于女人就是可信可亲的……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
如是,她的女主人公想,“绝不要爱情,爱情太无聊只会使人沉沦”。也许并不缺乏爱情的朱天文,眼神是清瘦的,不见容于世的,全然不似天心喜洋洋的人间烟火气。
胡兰成把朱天文与张爱玲相提并论,只是,张爱玲的温情背后裹紧了世故,她怀有的是一脉天真,是隔水听箫的凄清与空阔。
朱天文的文字华美剔透,有时却凌厉得可怖,亦纵情过度。
附录:朱天文创作年表
1972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强说心愁》。大学时创作的《乔太守新记》,获1976年联合报小说征文奖。还写有小说《淡江记》、《小毕的故事》、《炎夏之都》等。
1983年将获奖小说《小毕的故事》Growing up与侯孝贤合作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获第二十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风柜来的人》The Boys from FungKuei 1983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奖。
《冬冬的假期》A Summer at Grandpa’s 1984获第三十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瑞士罗迦诺国际影展特别推荐奖,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奖。
《童年往事》The Time to Live and the Time to Die 1985获第6届夏威夷国际影展评委特别奖;荷兰鹿特丹国际影展非欧美电影最佳作品奖。剧本获第二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
《尼罗河女儿》Daughter of the Nile 1987获意大利都灵第五届国际青年影展影评人特别奖。
《恋恋风尘》Dust in the Wind 1987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摄影、最佳音乐奖、葡萄牙特利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
《悲情城市》A City of Sadness 1989获意大利第四十六届威尼斯国际影展金狮奖。
《戏梦人生》The Puppetmaster 1993获夏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比利时根特国际影展最佳音乐效果奖等。
《好男好女》1995年剧本Good Men,Good Women获第三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极上之梦——〈海上花〉电影全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