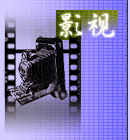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 编者按:孙绍谊这篇详细解读陈冲导演的《天浴》,言辞犀利,颇有几分大气,值得细细品位。 |
|
看完陈冲导演的处女作《天浴》,直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一时又无从说起。于是放在一边,想着再看时或许会有全新的感受。
这期间适逢大学老友李迅自美国东部游学回北京,顺道在洛杉矶歇脚。李君目前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且在藏片甚丰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述职,可算是大陆电影理论界承前启后的人物之一。承美国电影艺术学院陈梅女士的牵线,李君得以在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作了一次关于大陆电影研究现状的讲演。原以为陈梅女士漂亮的英文和李君对大陆电影理论的耳熟能详至少会引来十数个兴趣盎然的同道,没曾料到加上主办者,听众亦不到十人。于是联想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美国电影批评家们在中国大陆刮起的理论旋风,感触良多。
最近又读到关于张艺谋主动撤回其角逐本年度坎城电影节大奖新片的消息。在致电影节主席的信中,张艺谋批评了西方影人对中国大陆电影采取的绝对两元化态度:要么是政府宣传的喉舌,要么是怒目圆睁的反政府斗士。那些难以被划入这两个阵营的影片,无论在讲述故事和视觉表述方面具有多大的独特性,都不可能逃脱评委的冷眼。由于张的新片《一个都不能少》已顺利通过大陆官方的电影检查,并正在各大城市上映,因而显然不符关于两个相反阵营划分的预设立场,它在电影节上所能达到的效果应可料知。
两件看似孤立的小事,实际与中国大陆电影在全球市场中的旅行和消费有关。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第五代导演的兴起,大陆电影着实在世界上风光了一阵,加上港台两地电影的推波助澜,大中国圈内的电影业颇显蓬勃之气,张艺谋、陈凯歌和田壮壮等导演不仅是西方大学讲坛上时常提到的名字,而且也为一般西方影迷所称道,很有追赶黑泽明盛名的劲头。但在大陆电影所享声名的背后,已经蕴含了日后渐趋平淡的隐忧。细读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影片都以大陆厚实的历史发展为依托,或是加以寓言化处理,或是揭露其荒谬及残忍性,应合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界批判性地思辨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总体氛围。这些影片一方面为大陆赢得了不少国际赞誉,但另一方面却似乎在影像的全球性消费与旅行中为大陆电影做了定型化处理。第五代导演主观意念极强的"作者电影"以其蕴意丰富的象征和隐喻以及精心设计的视觉造型为大陆电影在国际影坛赢得了空间,却也不自觉地影响乃至造就了国际观众对中国大陆电影的预设观念。对普通西方影迷来说,中国电影就是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的片子;而对西方关注中国电影的批评家而言,"历史感"及"隐喻性"又似乎成了中国电影的注册商标,那些不能轻易与此类解读合拍的中国电影,当然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或关注。
早在1986年,美国文化批评家詹明信(FredricJameson)就在《第三世界文学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一文中坚称所有"第三世界文本"(电影当然可算一种文本形式)都必然是寓言性的,可以被解读成"国族寓言"(NationalAllegories)。这一断言似在拔高第三世界的文本表述,但却有意无意地否定了其个人性,仿佛第三世界国家除"国族寓言"之外不存在其它文化话语。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化,大陆电影同样面临着从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文化电影"向争取票房收入的商业电影的转型。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锐导演,如冯小刚、叶大鹰等,尽管他们的影片在大陆颇为轰动,但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像流通与消费中却了无涟漪,其中的缘由恐怕与西方观众与批评家对大陆电影的审美定势有相当大的关联。用一句话简单地概括:从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认识中国影片的西方影迷和批评家不知道如何对待那些以当代城市生活为背景、不刻意将自己打扮成反政府斗士、且又略带轻喜剧色彩的大陆电影。
拉杂许多,无非是想引入对陈冲处女作《天浴》的思考。再睹之余,首先浮出思绪的是,陈冲为什么会选中这样的题材作为改变其演员身份的第一抉择?电影史上演员从镜头前走到镜头后的例子并不鲜见。远的不说,大陆最近的例子就有以出演《芙蓉镇》、《本命年》和《红高粱》走红的姜文。但镜头前的光彩并不必然意味着镜头后的成功。正因如此,很多导演在锁定首部影作的题材时,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文化背景放在突出位置。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姜文并未象长于他数岁的城市青年那样背起背包上山下乡,对文革的经验也因为年幼而相对有限,但他在选择自己执导的第一部涉及文革的影片时,很机智地将镜头的焦点对准一群因父母卷入政治纷争而无暇顾及的北京军队大院青少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导演对虚构人物马小军的审美把握。实际上,马小军生活的年代和成长的经历也正是姜文这一代人的童年写照。张艺谋的《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尽管时间背景被推回到他所未曾经历的二、三十年代,但从导演分别将小说原作的地点山东和江南改写为西北黄土村落这一点可以看出,导演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成长氛围对其美学选择具有很深的影响。
《天浴》致命的弱点恐怕正在于导演对影片人物与环境缺乏切肤的体验。影片的叙述主线围绕一个文革后期响应号召到四川边远藏族地区务农的成都女孩展开。随着在政治鼓动下腾沸的青春热情的消退,下乡的知青们很快便为回城而各显神通。无钱无势的秀秀,此时正在离场部几十里之外的草原与藏族人"老金"学习牧马。为了达到回成都老家的目的,她先是轻信了场部孙供销员的允诺,为此失身,接着不惜以身体和青春铺垫回城的道路。但她的肉体奉献并未最终敲开回城之门。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堕胎后的秀秀让老金用枪弹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以死赎回了失去的天真与清白。这样的题材对六十年代初出生的陈冲来说,至少存在三重的隔阂。首先,尽管中央集权体制下渗透于各个角落的政治话语部分消泯了大陆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性,南方与北方以及沿海与内地之间在经济、文化、语言上的不同并未因政治上的大一统而消失。自小在上海医生家庭长大的陈冲面对川藏草原时所产生的"文化震惊,"大概不会逊于她初到美国时的感受。其次,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陈冲并未真正象影片中的秀秀那样上山下乡,没有经历过上一代人的政治热情以及随之产生的幻灭感。其三,陈冲属于大陆改革开放后有幸涉洋留学西方的第一批人。这些人的长处在于能够领风气之先,以比较的眼光透视大陆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其短处则是在未充分体会与思考中国文化的底蕴前即与其脱离,特别是未能置身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弥漫大陆知识界的"文化热"中。这三重隔阂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影片的感染力,使《天浴》既缺乏《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激情与狂放,又不具备《青春祭》、《盗马贼》等影片所表现出的对文革经验以及汉族文化的反思精神。
根据陈冲自己的说法,她不顾时空及文化隔阂而选择《天浴》乃是受到一个藏族女孩故事的感动。这个女孩被其部落选中,作为宗教献祭的牺牲。她的皮肤被用作鼓面,经打击而发出的鼓声成了联络人间与天界的中介。在与小说原作者严歌苓共同改编剧作的时候,她常常为川藏高原的广阔深邃而惊叹,每当遥远的歌声传来,她就不自觉地想起那个西藏民间传说中的姑娘。显然,陈冲有意让秀秀传达她对被当作牺牲品的藏族女孩的感动,同时亦通过秀秀在死亡中重获新生的故事控诉那个荒谬年代中扭曲的人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秀秀既非那个生活在宗教传说中的神秘藏族女孩,其世俗化背景又难于令观众将她和抽象于具体环境之外的宗教思辨挂钩。影片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秀秀在成都家庭和中学的最后日子,二是她在川藏高原农场的知青生活。无论从叙述结构还是从意念铺展角度着眼,故事的重心显然摆在第二部分。但颇为遗憾的是,相比之下,着墨不多的第一部分似乎较精心渲染的第二部分更具感染力。做广播体操、父母临行前的叮咛以及登车出发几场戏不仅突显出秀秀童稚未泯的天真和清纯动人的活力,而且运用文革音乐和才但卓玛歌声成功地烘托出那个已逝年代的氛围。象很多文革影片如《青春祭》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天浴》也以画外音开片,通过秀秀初恋男子对其中学生活的回忆引入全片的中心人物秀秀及其家庭。这种以画外音联结叙述的结构方式至少具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它赋予影片以自传色彩,用虚构的个人回忆拉近影像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由于画外音以第一人称出现,其叙述的权威性也就受到一定影响,但也正因为叙述观点的个人化,观众更易认同影片中的虚构人物,产生亲和力。第二,说话者与被说者之间可以产生某种"叙述紧张。"由于说话者是从他的观点讲述故事,被说者的心理活动也就暂时遭到悬置。观众只能通过说话者的视点揣测被说者的所思所想,从中得到审美快感。第三,叙述权威的削弱为反思整个叙述的客观性提供了契机,它可以使影片超出历史再现主义,揭示影像表述背后的话语性和建构性。可惜的是,《天浴》似乎并未充分挖掘画外音所具有的潜力,随着满载知青的卡车在歌声中逐渐远去,男青年充满感性的嗓音也渐渐消失,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之间初步建立起来的微妙关系随即崩溃。由于画外音的突然隐去,秀秀在川藏高原所经历的一切,包括看电影、与老金学放马、以肉体铺垫回城之路等,立刻失去了叙述的依托,使观众无法确定究竟应该怎样面对眼前晃动的影像。这并不是说说话者必须始终伴随叙述的铺陈,而是要求故事叙述一以贯之的完整性。观众完全有理由发问:既然叙述者并没有与秀秀一起共赴川藏高原,接着围绕秀秀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究竟具有多大的可信度?秀秀穿上军大衣准备奔赴川藏草原前、故事叙述者满怀惜别之情跑到教室二层目送其远去的一场戏本来为进一步发展二者关系作了铺垫,但除了秀秀在"天浴"前向老金炫示男孩送给她的万花筒以及影片结尾时忽然重现的画外音对这层关系稍稍有所交代外,全片自此都在叙述主体缺乏的情况下进行,失去了故事赖以成立的逻辑基础。同样以画外音开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不仅以马小军的叙述嗓音贯穿始终,而且通过莫斯科餐厅朋友聚餐一场戏的两次截然不同的讲述对回忆本身加以颠覆,逼迫观众从更高的层次思考叙述和话语的建构性,从而深化了影片的审美内涵。《天浴》弥补主要场景中叙述主体缺席的做法是在镜头转到秀秀开始草原农场生活时加上男孩的画外音:"有时候好久都没有一点文秀的消息。我就把从别的知青那打听来的故事编织起来,想象她在草原上的生活。"既然是"编织,"且又是"想象,"何以整部影片都似乎贯穿着不容质疑的叙述自信?
中国大陆自五十年代以来拍摄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影片,大约经历了两次转变。文革以前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一是将广西及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描绘成能歌善舞、男欢女快的族群,如《刘三姐》、《五朵金花》等;二是以阶级分析为依托反映藏族民众在"奴隶"制度下非人的苦难,如《农奴》等。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影片,在反思文革经验和"文化热"的总体社会氛围影响下,重新定义了"少数民族影片"的意义。它们不再热衷于展示"异域风情"和图解政治宣传,而是通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反思汉族文化,直接或间接地批判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文明。《青春祭》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知青影片中脱颍而出,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在于它能够超越对文革经验非善即恶的两元思维,沉思汉族文化以及人性的复杂与矛盾。影片开始时女主人公在傣族老人引领下穿过森林的一场戏,本来为谴责荒谬年代的政治做了铺垫。但影片并未纠缠于伸张道德的义愤,而是以女主人公与傣族家庭和傣家姑娘之间关系的转变揭示大荒谬背景下知青群体对那断特定岁月的复杂情感。毕竟,他们在那片远离城市的土地上留下了火红的理想与多梦的青春。影片结尾女主人公重返傣乡,面对秀山绿水而情不自禁的感动与追怀,恐怕不是简单的非善即恶的逻辑所能解释的。应该看到,《天浴》在处理藏族青年"老金"和汉族少女秀秀的关系时,也或多或少含有对汉族文化的某种批判。除了秀秀、秀秀家人和她的初恋同学外,老金恐怕是影片中唯一的正面人物。与场部汉族干部利用职权之便索取肉体占有相对,老金对秀秀的家长般的体贴代表着人类高尚无私的关爱。影片中老金两次为秀秀持镜时面部表情的微妙变化,既显示老金对这层关系的无怨无悔,又透露了他对秀秀近乎主动的献身的鄙夷。那面残破的镜子不仅让秀秀和观众反观自身,而且亦折射出被功利和欲望玷污的汉族文明的虚伪一面。遗憾的是,《天浴》似乎并未进一步深入开掘秀秀与老金之间因偶然机缘碰撞产生的文化冲突。纵观全片,秀秀始终纠缠于回城的情结之中,没有也不可能对川藏草原的广阔深邃和以老金为代表的藏族文化加以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思索。影片结尾时的饮弹身亡,仅仅体现了秀秀对肉体奉献后仍满足不了回城要求的绝望,并不构成对汉族文明的挑战和颠覆。而脱离了具体文化和民族背景的老金也很难作为反思汉族文化的参照。正象他生理上的"缺乏"一样,部分汉化且又孤立存在的老金也象征某种文化的"缺乏。"如果说《天浴》可以勉强被划入"少数民族影片"的话,它只能被看成是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以来同类影片的下乘之作。
回到全球影像流通和消费过程中中国影片的定位问题。陈冲选择《天浴》作为其导演的处女作,恐怕不单是因为她受到那个关于藏族女孩传说的感动,更深一层的缘由似与国际评委和电影节对"中国电影"(或从广义角度而言,关于中国大陆的电影)的前设期待有关。熟谙好莱坞电影制作发行和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的陈冲,应该知道象《天浴》这样的影片,既不可能跻身于美国主流影院,又不可能吸引生活在文化与经济转型中的大陆观众。因此,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电影节就成了该影片的"期望观众。"多年来,电影节作为一种机构化了的组织,一方面在本地影像的全球性流通以及发现好莱坞之外的民族电影等领域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某些因机构化而形成的预设立场以及或明或隐的成见与限制。前面提到,中国大陆影片由八十年代在重要国际电影节上屡屡获奖到九十年代末的风光不再,个中的原因恐怕与某些电影节对第五代导演乃至整个中国电影的预设期待不无关系。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对张艺谋撤回坎城影展参赛片颇有猜测,认为背后可能有中国政府的参与,但从张本人对《一个都不能少》的高度评价来看,他显然对坎城影展某些评委将其标签为"政治宣传"感到不悦,意图以撤出影展角逐突破某些国际电影节对中国影片的预设期待。与张艺谋相反,陈冲似乎更渴望以自己的影片满足某些电影节对关于中国大陆影片的期待。文革经验和对共产党政府的批判可以给影片打开某些影展的大门,而敏感的西藏问题更足以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尽管如此,无论从电影艺术角度还是从电影史方面着眼,《天浴》将只能被证明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作者简介:孙绍谊,美国南加州大学文学博士,电影理论硕士,现在南加州大学东亚语文系任教,讲授亚洲文学、电影课程。
原文刊载于台湾金马影展评论集《电影档案》第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