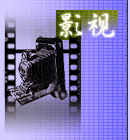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 编者按:绝对点说,今天的法国电影没有一处不来自传统。影响今天法国电影的传统有很多,戏剧、文学和自由的创作的圈子风气,法国知识分子的参政愿望和20世纪的法国哲学等等,但总体来说,最直接和最具体的影响则来自于新浪潮运动、左岸派和“五月风暴”。 而这其中新浪潮毫无疑问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分析一下新浪潮的前因后果…… |
|
“有一点我们强调得不够:‘新浪潮’既不是一场运动,也不是一个学派,又不是一个集团,它只是一定的量,是报界创造出来的统称,为的是把两年来崛起于本行业中的五十余名新手统归一类,以往,每年只能出现三四名新人。”
——弗朗索瓦.特吕弗 《法兰西观察家》1961年10月19日
“……不过,这的确是一段好光景。既然这一套吃掉开,制片人当然都希望拉青年人为白己拍‘新浪潮’影片.
——米歇尔.德维尔 《正片》,第58期,1964年2月
1958年是法兰西历史也是法国电影史的转换点。
1958年5月至9月,政局动荡,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行将消亡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戴高乐当选总统前的法国。——译者……有一位慈父将亲自出马,把法国人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从奇耻大辱中拯救出来。法国人真是三生有幸。
大体与此同时,电影出现了更新的迹象,这在文艺沙龙中引起了反响,随后,各大报刊便把这种新动向冠以美名“新浪潮”。
新法国要新电影。口号应运而生。当然,无论是法国,还是法国电影都没有象当时宣扬的那样明显改观……这也无妨,1958年毕竟算是转折的一年。
“新浪潮”这个名词一直洪福不浅,至今人们还在谈论“ 新浪潮”影片、“新浪潮”时期,或是抱有敌意,或是带着怀旧情绪。一位才能有限,但富于想象力的制片人,为了发行放映比埃尔.德朗雅克的《寻枪记》,甚至于1966年某一天举办了“下一次浪潮日”,虽然这部影片不久便无人问津。“新浪潮”——这就是电影。
然而,“新浪潮”的出现有着远为广泛的背景。要想了解它的起源,应当追溯到1957年10月3日出版的一期《快报》。这一天,在周刊封面上印着一位妙龄女郎的面部特写,标题是《新浪潮来了》,下面引用了夏尔.贝玑(夏尔.贝玑(1873—1914):法国诗人、政论家。曾在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案中主持正义,为德雷福斯辩护。所写作品有剧本《贞德》、长诗《夏娃》等。 1905年后发表《我的祖国》一书,宣扬沙文主义。——译者)的箴言:“我们才是中枢和心脏,中轴线从我们这里通过。要以我们的表来对时”。当时,正在开展广泛的全国性征询活动,总共提出了二十一个问题。自10月10日至12月12日,《快报》周刊连续登载了回答与分析文章,从中总结出来的《全国青年问题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新浪潮”的提法一直与《快报》联系在一起,甚至从1958年6月26日至12月 11日,各期《快报》的封面都印着副标题;《新浪潮期刊》,前后达半年之久。……那时,还尚未涉及到电影。
“新浪潮”这一名词见诸报端,多半是弗朗索瓦兹.吉罗(吉罗(1916一);法国女作家,《快报》创始人之一。后任激进社会党副主席,曾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妇女部中任要职。著作有《新浪潮》、《青年肖象》、《假若我在说谎》、《权力喜剧》等。——译者)涉笔成趣的产物。而电影开始凑趣则是数月之后的事。这家《快报》在1958年10月30日出版的一期上登出由影片《我们都是杀人犯》(影片摄于1952年,导演是卡雅特。——译者)的导演署名的一则启事,标题是《您愿为卡雅特的影片出力 吗?》启事内容是:“拜读过‘新浪潮’之后,我决定拍摄一部这类题材的影片。我在幕前,诸君在幕后。本人成竹在胸,诸君则希望有人代言……候回音,烦告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八十一号,《快报》周刊,安德烈.卡雅特先生”。果然,报社收到了一些回信,并登在 1958年 11月 2 0日的《快报》上。许多回信强调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并且殷切希望在银幕上对其有所表现。(在1957年春季进行的调查中,有个问题是:“对法国人来说,全国头号难题是什么?”在“新浪潮”青年的回答中,阿尔及利亚问题居首位(百分之二十八),其次是“找一个稳定的政府”(百分之二十四)。这两个问题在随后四年期间也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而所谓“新浪潮”影片对此只有寥寥无几的反响。——原注)这件事未见下文。倘若安德烈.卡雅特的影片果然拍成的话,世人所知的“新浪潮”想必就不是如今这个样子了……
后来,历史为“新浪潮”一词保留了特定的含义,最初将“新浪潮”用于这个含义上的人大约是彼埃尔.比雅尔。他在《电影》1958年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汇报,题为《法国电影的青年学院》,他列举了青年导演的一份名单,名单之驳杂,二十年后当令人捧腹(1918年后出生的导演一律算做“青年”:韦纳伊、博尔德利和雷卡梅竟与路易.马勒并列,而象阿仑.雷乃那些“拍短片出身的导演”和“电影手册派”的里维特、特吕弗、夏布罗尔还榜上无名呢),比雅尔最后断言。“这股‘新浪潮’为什么还服服贴贴地跟着前辈转,真令人困惑。”
不过,直到1959年春季,围绕着基纳电影节和在拉纳普尔的青年导演的聚会上,电影“新浪潮”才确实名声大噪,并从此叫开了。
倒叙
可以沿着两条平行不悻的路去寻找“新浪潮”的根。
一是,当浪潮已过,前景已经分明之时,一些有名望的前 辈要求承认他们在“新浪潮”中的一席地位。电影史学家是承认阿涅斯.瓦尔达(1954年他拍摄了《短岬村》)或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1955年拍摄了《狭路相逢》)的先锋作用的,或许还承认让一比埃尔.梅尔维尔是前驱,他也大言不惭地以此自居:“‘新浪潮’,这是新闻记者的发明,……新导演所做的事,我在 1937年就打算做了。遗憾的是,直到1947年拍出《海洋的寂静》之后,我才实现了宿愿”
另一条路子同样值得注意,那就是,与同辈人一起,回顾一下在掀起“新浪潮”之前的几个月中法国电影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些变化的感受。
还必须提及《快报》周刊。在那几年,这家周刊相当及时敏锐地反映出年青人的思潮变化。1958年1月30日,《快报》封面上刊登了影片《通往绞刑架的电梯》男主角莫里里斯.罗内的剧照,并引用了路易.德吕克的一段题词:“今后,不仅仅是循规蹈矩的孩子去摆弄影象了”。同年,3月13日,德尼斯.温桑著文分析爱德华.莫利纳罗的影片《背倚高墙》:“多年来,无论哪一家法国制片厂拍出的影片都象是陈年旧货,粗糙不堪,可是这部影片与众不同。年青一代导演正把埋头苦干令人感动的老家伙从摄影机旁赶走,他们要亲自动手,以克鲁佐或贝克为榜样,大量拍片。这些年轻人多么精明,记忆力多么强!甚至有些过分……”
这一年11月6日,弗朗索瓦.勒代利埃谈到不久前拍摄《恋人们》时的情景;“……只有当一个摄制组在导演身上感觉到对新电影的坚定信念和至少不照搬时下影片老套子的坚强意志时,才能发挥出这么大的干劲。总之,人数这样多的一班人马(近三十人)好歹得适应拍一部短片的物质条件。……效果如何,这要由观众来判定,不过。这种方法表明,在法国电影中,正出现某些变化。夏布罗尔 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的摄制组的人数也大体相同。”
一周之后,在同一版面上,丹尼.温桑更是把握十足地划分了阵营:“为企业获益,按生产处方炮制的盈利片最好也不过是《厄运临头》(《厄运临头》拍于1958年,导演是乌当.拉哈,主演是碧姬.巴锋。一一译者),最劣就会是《马克西姆》一类影片,而与此同时,平行电影正在诞生,因为有些人已经感到,电影的革新不在于用变形镜头拍摄宽银幕,不在于色彩,也不在于任何技术上的进步,而是来自‘内部’;这些人大多数是青年……不错,这种脱离传统道路的作法所以能出现,多半是受了1955年12月设置的优质奖的激励。”(法国文化部设置该奖鼓励有创见的导演。——译者)
1958年岁末,法国人更换了政府(他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也换了总统,甚至连共和国也改了号,取赞成态度者过了大半(百分之七十九点二五选票同意戴高乐新宪法,仅有百分之十五弃权);而且,他们被告知;法国人的电影也要变!
概述
“新浪潮”就是在 1958——1959电影年度期间问世的,其标志是:克洛德.夏布罗尔的头两部影片在商业网公映(1959年2月2日,《漂亮的塞尔杰》公映,1959年3月11日,《表兄弟》公映)、特吕弗的《四百下》和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对这四部影片的介绍均参阅。电影艺术译丛》 1980年第 1、 2 NI期刊载的、法国“新浪潮”和“左岸派”。一文。——译者)于1959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放映。从1961年起,便有人宣称“新浪潮”已趋低落。路易.马尔科列尔在1961年10月17日《法兰西观察家》报上甚至写道:“现在我们可以说,‘新浪潮’已经终结…” 我们认为,“新浪潮”做为社会经济现象总共延续了四年,这大概是不错的。它的崛起是在1958年,到1962年期间便自行削弱了。
如果我们只限于综述事实,不加评论地概括“新浪潮”现象,它就应当包括两类情况。一方面涉及影片,另一方面涉及围绕电影大作文章的报刊、新闻和评论。
首先是电影。上述四年期间,至少有九十七名导演拍摄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这足以使专业人员和公众舆论大为震惊。新闻报刊便跟着大事宣传。严肃的刊物注重提高这一现象的意义,并且对它加以分析。而发行份数较多的报刊只图保留“新浪潮”这个合适的商标,然后慷慨大方地四处加封:从影片到导演,从大明星到影坛新秀。“新浪潮”有销路,大家都搞“新浪潮”,为了内销,也为了出口。影片与围绕着影片的沸沸扬扬的推销活动混杂在一起,很快便难分彼此了。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事正紧,舞文弄墨“毒化空气”成了时髦。于是,围绕着“新浪潮”,人们又开始毒化空气”了。
“新浪潮”与法国政局的变化同期发生,实在纯属偶然。即令第四共和国延续下去,仍然会出现“新浪潮”。下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现象有其必然性,而且,即便在另一个政治背景中,一系列具体原因也会促使“新浪潮”出现。但是,法国动荡不安的局面(或许这只是动荡的幻象)毕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需要新人、新形式、新语汇。各家报纸对这种动荡的局面自然求之若渴。“销售畅旺”的就是金融界新巨头、戴高乐讲话、长筒裙、“新浪潮”一类消息。为了显得在行,“新浪潮”干脆被简称为N.V.”(法文“新浪潮”两词的第一个字母。——译者)
“新浪潮”是个来势汹汹、波及甚广的现象,现在应试将汇成“新浪潮”的不同分支加以区别。
我们似应回顾一下第四共和国时期已经僵化了的电影。当时,电影创作者相对来说已为数不多,而且许多人已经上了年纪,因为自第二次大战以来,人材更新十分有限。具体来说,1958年,马克斯. 路 尔已经去世,雅克.贝克、让.格莱米水也只有几个月的光景了。让.雷诺阿、雷内.克莱尔、阿贝尔.同斯、萨沙.居特里、马塞尔.帕涅尔(文中所提导演是二十年代以来法国影坛的大师。——译者)都是年迈老翁,到了创作生涯的末期。1957至 1959年是较为次要的,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最多产的十二名导演拍完了各自的最后一部影片,他们是雷蒙.贝尔纳尔、安德烈.贝多米奥、马塞尔.布利斯丹诺、莫里斯.德卡依日、亨利.迪阿芒一贝尔热、乔治.拉贡布、列奥尼德.莫居、让.斯特利、罗贝尔.维内……为了保证法国电影能继续在各方面生存下去,把担子交给在次要岗位上等了十年左右的人就是必然的、刻不容缓的事了。总而言之,由科班出身的人来接班是势在必行。
在第一类新崛起的导演之中,爱德华.莫利纳罗是个样板。他生于1928年,先是为莫里斯.德卡依日、安德烈.贝多米奥做过助手,后来拍过纪录片,搞了十年专业之后,才战战兢兢地尝试拍摄故事片(《背倚高墙》)。1959年5月10日,他在拉纳普尔讨论会上做了发言,指出自己在“新浪潮”中的地位,颇有自知之明。他说:“以我之见,似乎应当把所谓‘新浪潮’一分为二,一方面是通过正规途径进入影坛,即融入正规制片系统的青年导演;另一方面,是终于博得年青的制片人或因外人士的信任的一批人。我想,假若没有特吕弗或夏布罗尔,我们这些从正规途径走过来的人,仍旧是电影界正统‘官员’。现在,既然他们的电影已经问世,我本人也算有幸,我的 下一部影片就不至于太蹩脚。固然,十年来,我不得已拍出那种风格的影片,这是出于无奈,那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而明年,我要改变拍法。”
爱德华.莫利纳罗并没有改变拍法。一旦“新浪潮”的狂热趋冷下去,他便成了第五共和国一名地地道道的电影“正统官员”,他的电影年表上列着二十四部影片(这个统计数截止到1978年。1980年,莫利纳罗又拍了一部影片。《疯女牢笼》第二部。一译者),是近二十年来最长的电影年表之—……
在“新浪潮”中,与莫利纳罗同时开始拍故事片的科班导演有两、三打人,如,比埃尔.格拉尼埃一德费尔,他当过让一保罗.勒沙诺瓦、安德烈.贝多米奥或马塞尔.卡尔内的助理导演;乔治.罗特奈,他当过场记、剪辑、摄影师和诺贝尔.卡尔博诺的助理导演;雅克.德莱,他曾经是让.鲍育、吉勒.格朗热埃、路易斯.布努艾尔、儒勒、达森的助手。在这份人名表中,似乎还应添人象克洛德.索泰、让.吉罗尔或路易.马勒那样与众不同的人物。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涉足故事片是他们“修业期满”之后的归宿,虽说苦熬多年,却也必不可少。
有些人发现自己也被赐予如此时髦的美名之后,大感惊讶.米歇尔.德维尔在数年后就曾流露出这种心情:“我是循着传统老路一步步走过来的,这正是我与‘新浪潮’不同之处。最初,我当过见习导演,然后是第二助理导演,并且做过德古安的第一助理导演,后来又成了技术顾问。拍完《今夜不再来》(该片摄于1960年。--译者)之后,有人说,我属于‘新浪潮’,我大为吃惊。在编写剧本时,尼娜.孔巴涅兹和我都深信我们是和‘新浪潮’对着干的。”(见《正片》,1964年2月,第五十八期。——原注)短片起家
(短片包括纪录片、科教片、实验影片等。——译者)
他们可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们无疑是众望所归:阿仓.雷乃、乔治.弗朗朱,还有比埃尔.卡斯特、亨利.法比阿尼、罗贝尔.门 戈兹、让.多埃维,以及其他人……五十年代末,电影俱乐部活动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些拍短片的人被介绍、被承认了。著名影片有《巴黎残老军人院》和《禽兽的血》(乔治.弗朗朱)、《战祸》和《被诅咒的建筑师》(比埃尔.卡斯特)、《弥天大罪》、《我的雅奈特及我的伙伴》、《住宅危机》(让.多埃维)……当然,还有阿仑.雷乃的《梵高》《高更》、《格尔尼卡》、《夜与雾》和《世界的所有记忆》。本文无意撰写三十人小组(三十人小组指阿仑.雷乃为首的拍摄纪录片的一批人,到 1958年 12月,这个小组的成员已达一百二十三人。——译者)的历史,只是应该强调指出,十年来,短片为法国有所抱负的电影争了光,也是它的容身之地。
这些人拍的短片从来广泛放映过。或者,只是做为一部商业片的“加片”才有广泛放映的机会,观众反应则是冷淡和不耐烦。而影片《夜与雾》是唯一的例外。这部影片在1957至1958年期间驰名遐迩,外省的观众所以赶去看卢奇阿诺.埃麦尔的意大利片《重婚》,就是因为他们得知要加映阿仑.雷乃的《夜与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特别是通过电影俱乐部、报刊杂志、电影节这些文化网的渠道,人们了解到,在法国,不仅仅有德拉诺瓦,也不仅仅有德尼.德拉巴特利埃(德拉巴特利埃(1921一),主要作品有《开往杜布鲁克的出租车》。---译者)来接替德拉诺瓦。人们对阿仑.雷乃寄以厚望。人们期望他和其他电影导演拍出一种左倾电影。因为,不言而喻,从几部短片来看,阿仑.雷乃和其他几个导演就是左派;而第四共和国大多数导演“背叛了”现在,躲进趣闻轶事或古装片中偷生。通过那些短片才能在银幕上看到当代法国人的生活,看到住宅危机,看到矿工罢工……
也正是在这些短片中,新风格渐趋形成,电影避免了特吕弗曾经痛斥的过分精雕细琢的叙事方式。这些短片可以是实验作品,可以笔触大胆,揭露时弊。而在1957年“功成名就”的电影中痛感缺乏的恰恰是这些特征。
当然,三十八人小组中的佼佼者转行拍故事片也不是很有把握,即使比埃尔.卡斯特曾经战战兢兢地指过路(在这些人当中,比埃尔.卡斯特是第一个拍故事片的人,1957年他拍摄了《袋中爱情》----译者)。不过,由于观众的进步、大城市中专门性电影院的建立,而出现了新需求。国家又通过预付收入的办法进行资助,给予了最初的推动。从1957年5月起,各大报刊一呼百应,纷纷报道了阿仑.雷乃即将在法国和日本拍摄有关原子弹的大型记录片的消息……(“大型纪录片”一语系原报道所用、——原注)
异军突起
什么是史实,什么是经过渲染的传奇,在这里最难分辨。《电影手册》的编辑们早有亲自大干一场的打算,他们也从不讳言。其中几位已经在所谓的电影“专业”中立足了,因为这里的界限并不分明。比如,克洛德.夏布罗尔曾经担任二十世纪福斯公司新闻专员(当时夏布罗尔负责为美国影片的法文版编过新片名.——译者),后来,他还把让一吕克.戈达尔和保罗.日戈夫引荐进来(日戈夫有一段时间替夏布罗尔写剧本,后来拍过一部《落潮》,这部影片也如“新浪潮”时期许多影片一样胎死腹中)。有些人尝试拍过纪录片,不过成就不一(如,雅克.里维特的《牧羊人的运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顽 童》)。继承遗产、有油水的婚姻——这些偶然机会也为他们一下子提供了必需的资金去“筹划”第一部故事片。影片未及问世,他们就开始大吹大擂,以至于“新浪潮”一词的意义从此在大家的默许下变窄了。结果,这些冒牌的业余爱好者们便把“新浪潮”旗号据为己有。影片一部接一部,他们赚了些钱,开设了制片公司 (如,克洛德。夏布罗尔开办了阿吉姆制片公司,后来这家公司为菲利普.德布罗卡、埃立克.罗麦尔、雅克.里维特的最初几部故事片提供了全部或部分投资)。不久,连较保守的制片人也嗅出了生财之道、千载难逢的良机和政洽气候(克洛德.夏布罗尔说过:“我们千万别上当;各大报刊哗哗不休地谈论我们,这是因为他们打算把一则方程式强加于人:戴高乐=革新。将军来了,共和国变了,法国再生了、电影和其他领域一样。看吧,天才崛起,知识分子在双十字微的庇荫下发挥才干。青年人有用武之地!”,----原注),于是,也开始为低成本的影片投资。
两年内,这家黄皮刊物的编辑们几乎都到摄影机后面去了:克洛德.夏布罗尔和弗朗索瓦.特吕弗,然后是让一吕克.戈达尔、雅克.多尼奥尔一瓦尔克罗兹、埃立克.罗麦尔、雅克.里维特、克洛德.德热夫莱。在他们的提携下,一些亲朋好友也连袂而至,譬如,菲立普.德布鲁十、让.欧列尔、弗朗索瓦.莫雷伊、列奥纳尔.凯热尔或让一路易.里查德。
比埃尔.卡斯特则另当别论。他不完全属于“新浪潮”一代(除了十二部较有名气的短片之外,在1957年,他已经导演了由让.马莱主演的《袋中爱情》,当时,这还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传统影片),但是,他与“新浪潮”的各个分支都有瓜葛:他作为格莱米永的助手修完了传统的“学业”;他又是三十人小组的成员,是人们翘首以待的左派;最后,他还是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记者,他为《电影手 册》撰写过不少文章,结果,《电影手册》派便不知羞耻地把他拉入自己的名下,这与他们把拍《广岛之恋》时的阿仑.雷乃归入自己一派的作法同出一辙。
1959至1960年间,全是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这或许是存心,或许是无意。每个制片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新浪潮”影片,有自己的新导演。在这股无法驾驭的游涡中,处女作竟有数十部之多,可是,其中不少影片从来就没放映过。当时,在选择应召待聘的导演的标准中,内行与否是最末一条。
这种含糊混乱的局面很快便与“新浪潮”这个称呼联系起来了。对“新浪潮”运动阿谀奉承的人往往也是运动的干将、他们在《电影手册》或《艺术》周刊上大肆吹嘘不受章法约束的格调、吹嘘戏嘘之中不失潇洒的风格、吹嘘与制片人或工会的刻板传统的决裂……他们为用少量投资就能上马而感到洋洋得意,他们有着无穷的幻想。在拉纳普尔讨论会期间,制片人亨利.多施麦斯特也来乘机赶浪头,他在《艺术》周刊上写道:“每个制片人都为‘新浪潮’的年青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因为是他们把电影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使电影摆脱了行业工会强加于人的最起码的摄制人员人数的限制。他们使电影从管理与财政上的困境中脱身,直接到街头、屋内实景、真实的住房和自然景物中去拍摄。他们把电影从层层审查关卡中解放出来,这种审查机构对艺术、对生活、对道德,对如何影响青年人,对维护民族尊严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实在荒唐。他们打破了‘老前辈们’拍片时的清规戒律。他们破除明星崇拜,摒弃单纯追求技术完美的做法。”
以不谙业务为骄傲。夏布罗尔说过:“为了处理《漂亮的塞尔杰》的第一个镜头,我还要问,我应该盯住摄影机的 哪一个取景器,我甚至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瞧!”夏布罗尔在拉纳普尔讲的这件趣闻或是确有其事,或是笑话一桩,这倒无关紧要,它毕竟表明了,在1959年,以外行自居是多么心安理得,甚至以此为荣!
在“巴尔纳斯电影院” (指专门放映艺术实验影片的一些影院。——译者)或巴黎电影资料馆中学到的电影文化保证了这些新教徒们不至于染上过分严重的陋习,至少,在一批影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之前,他们是自以为是的。开始是让一达尼埃尔.波莱的《瞄准线》找不到发行商,这是法国电影中最著名的“从未露面”的影片之一。可是,这位让一达尼埃尔.波莱就在拉纳普尔讨论会上还摆出过教训人的架势:“我有机会随心所欲地拍过一部影片。…我相信,用什么题材都可以拍出精采的影片来,因为,电影是在摄影平台上开始的,而不是在写剧本的时候。我拍了一部有价值的最无所顾忌的影片,但是,为了至少证实我对电影的看法不错,我愿意拍一部有规定题材的影片,只要由我物色演员,拍片时给我充分的自由。因为,至少就电影而言,敝人并不相信题材重于一切,而只相信画面、相信视觉印象,并且要以诗的方式传达出来,摆脱戏剧和文学的影响,以便易于接受音乐、舞蹈、绘画和诗歌的影响。我相信,如果说我们之间有共同点的话,那它无非就是对题材的蔑视。”
落潮
自 1959年岁末起,分歧的意见便开始出现了。法兰西文学报》曾连篇累续地报道“新浪潮”,影评界年高望重的权威乔治.萨杜尔在这家报纸上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介绍过让一吕克.戈达尔的第一部故事片(《精疲力尽》,这是六十年代的《雾码头》)。可是到1960年春天,《法兰西文学报》请菲利普.埃斯诺尔写了一篇法国电影 专论《可能成为艺术的企业》,文章惊动一时。他写道:“目前,这代人的唯一杰作就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海报巧妙组织的宣传仗,其目的是向迷信神童的公众灌输空想,似乎返老还童的奇迹正呈现在你的眼前……如果对影片<危险的联系>(<危险的联系>拍于 1959年,导演是拍过风靡影坛的<上帝创造女人>的瓦迪姆。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也认为影片<危险的联系>歪曲了德拉克罗的原著,把原著中的自由思想和对腐败的上流社会的描 嬗 俗化。小说译名为<风月笺>。影片男女主角由 钱拉.菲立浦和让娜.莫罗扮演。——译者)老朽不堪的内容用心思索,你便还会发觉,在这个由老年人统治的国家中,大家多么喜欢拍冒牌青年的马尼。我们情愿抛开所有这些电影界的菲力克斯.卡雅尔,他们简直比亨利.格依博士还老朽!(菲力克斯.卡雅尔(1919—1970)是 1957年新任的财政部长;亨利.格衣(1884-1970)于1948年至1949年期间任财政部长,后担任过两届总理。——译者)…… 不过,如果这些恶劣野心家的所做所为尚属有益无害,我们仍可大大地原谅他们。遗憾!一切表明,他们秘而不宣的希望就是撬开商业电影的大门,挤走被他们大肆低毁的人。他们拍的是低成本影片,但是,他们梦想有朝一日搞出宏篇巨制;他们蔑视明星,直到有一天能付得起明星的酬金。”(见1960年 3月17日、法兰西文学报。——原注)
对新浪潮电影导演的指责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人们指责他们拒绝采取政治立场(弗朗索瓦.特吕弗在共产主义大学生创办的《光明》月刊上著文宣称:“做为一个人,应当投票选举,艺术家则不这样做。他不能这样做……在法国有共产党艺术家,应该要求他们拍工人电影……我拒绝把爱与资产阶级或警察对立起来。警察也会有爱情……”)。报刊杂志从让一吕克.戈达尔那儿搞到的连篇累牍的言论就是集笑话与内 疚之大成。(可参阅1960 年6月16日至1961年7月27日《快报》周刊。——原注)假若《电影手册》派的影片不是象现在这样表现空虚与无能的话,那至多也只能表现一些意外巧事或次要现象。
但是必须记住,这是最糟糕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酷刑拷打、夏罗诺事件(1962年2月8日巴黎群众示威游行反对秘密军组织,在地下铁道夏罗诺车站发生惨案。——译者)、秘密军组织、被《当代》杂志称为“目无尊长”的极左分子的骚动使一代学生受到震动,克洛德.夏布罗尔的《表兄弟》却没有如实地表现当时这些学生的形象。况且,克洛德.夏布罗尔后来也承认,他的一部分创作灵感是回忆起巴黎法学生联合会(巴黎法学生联合会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右派学生组织。一一作者)时出现的。夏布罗尔在让一玛丽.勒邦(勒邦在1949年至1951年任该组织主席。她在1974年竞选过总统。——译者)和雅克.多米纳蒂担任该组织正、副主席的时候常参加活动。他写道:“在大学生的一次家庭晚会上,布里阿利(布里阿利扮演《表兄弟》中的男主角,这一段文字是影片中的一个场面。——译者)戴着德国党卫队军官的大檐帽,挺着腰板,象个普鲁士枪骑兵,他举着蜡烛台,扯着嗓子朗诵德文诗,这时,瓦格纳的音乐不绝于耳……我联想到勒邦具有的那种新纳粹色彩,诚然,这种色彩并不浓厚” (见克洛德.夏布罗尔著《但是,我在拍电影》一书.——原注)。克洛德.夏布罗尔当然算不上极右人物,但是,他的前几部影片(至少要包括进影片《老妇人》)还充斥着旧情节剧中的无聊的天主教教义(过失、补过、赎罪……),这些影片与当时大多数人的日常所虑大唱反调,因此,散布了右的情绪,这是不容争议的。影片《老妇人》表现出极端鄙视女人的情绪,这对某些观众来说无疑是一记耳光,因为,西蒙娜.德博瓦尔(西蒙娜.德博瓦尔(1908-):法国女作家,萨特的夫人,主张妇女解放的活动家,主要著作有《第二性别》。-----译者) 的理论已经开始在他们中间流传……如果说,在这里,我们只考虑到学生界或“有教养的人士。的反应,那只是因为“新浪潮”电影主要是在大学城中放映。它是专门为自命不凡的“精华”拍摄的。“新浪潮”是名流和学界的电影。到1961年,公开宣称不问政治已经不吃香了。
人们还讥讽那些自诩为“新浪潮”的影片在技术上或美学上贫乏简陋。这是第二种指责。在影片《精疲力尽》的年代,形式上不拘章法尚能博人一粲。这是作为对充斥五十年代银幕的平庸的匠气十足的电影的反动(如亨利.德吉安或吉勒)。让一吕克.戈达尔的跳接、逼真的录音令人耳目一新,犹如爽身的淋浴。笨拙却惹人喜欢。但是后来这种松散的手法被领路人与追随者到处套用,厌烦便很快替代了新鲜感。串通一气的作法(用导演圈里的朋友扮演配角、编辑部的人拍的每部影片都有硬加上去的一期《电影手册》的镜头)也失败了。人们发现,这些影片是靠搬用经典作品的一系列段落拍成的,在电影资料馆就可以看到这些经典作品。
罗贝尔.贝南戎(罗贝尔.贝南戎是法国影评家。——译者)挖苦说:“把探索加以神化的做法是为了大肆吹捧初露端倪而尚未成型的东西”,他不留情面地指出,一部分“新浪潮”导演在创作过程中还处于学习消化的阶段。他说:“…在摘抄式的影片中,希区柯克的一场戏接入布努艾尔的另一场戏,序幕之后便是维果的一个很长的段落,而这个段落又是按罗西里尼的精神拍摄的,并且还用上了切夫斯基(切夫斯基(1923—1981):美国剧作家,他把电视的写实风格引人电影,作品有《马蒂》等。——译者)的技巧使影片显得年青。这种兼收并蓄可谓食欲过盛的表现,它反映出人们对营养学确实津津乐道。怪不得他们对
贝克的影片中吃肝糜的一场戏备加赞赏。他们也大段大段 地拍过早餐、快餐或宴会。不过,当创造活动被摄食活动代替的时候,食人生番所熟悉的现象便会出现:食者以为他吃下去的东西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见罗贝尔.贝南戎《皇帝赤身裸体》一文,1962年6月第46期《正片》。——原注)
结论
二十年后,新闻界的大事宣传早已被忘却,最初的崇拜者的那股狂热已经消失,理智和刻薄的人共有的恼怒情绪终于平息,“新浪潮”现象也被纳人比较合理的范围中。“新浪潮”是一段接班时期,它显得很混乱,连篇累族的夸大其辞的评论掩盖了它的真相,凑巧,它又与政治动荡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政洽动荡也是被革新的空喊吹得神乎其神……两年后,“新浪潮”便溶汇于电影整体之中了。重新站队,重新选择,这涉及到所有的青年导演。许多人渐渐地被淡忘了,甚至永远匿迹影坛;另一些人实质上成了追求技巧完美的导演,与《电影手册》曾经那样激烈地抨击过的导演别无二致。克洛德.夏布罗尔和弗朗索瓦.特吕弗一直在搞最程式化的影片,他们与科班出身的爱德华.莫利纳尔、雅克.德莱、乔治.娄德耐并肩前进,一部影片接着一部影片,一块砖接着一块砖,列出了第五共和国最可观的影片目录……
总之,“新浪潮”是个发射台,它把那些既不在助手的“跑道”,也不在短片的“跑道”上的人引上了拍摄故事片的航路。
……“新浪潮”至少有一个积极的贡献:摄制班子不臃肿、在实景中拍摄、不拘泥于过分僵化的专业规则…这种解放思想的作法影响了以后的年代。那时,在电影开始起步或正在复兴的国家中,青年导演们最希望掌握的就是这方面的经验。正是由于这几点确实摆脱了陈规旧习的思想,“新浪潮’才成了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