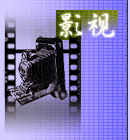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 编者按:只有少数老资格的影迷才会记得1968年那个令人陶醉的日子。新浪潮的中坚力量:特吕弗和戈达尔给当年的戛纳电影节的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从携手同行到分道扬镳,这中间有太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
|
 前几日在报纸的电影新闻重逢戈达尔,那是从戛纳传来的消息,戈达尔的新作《我们的音乐》(Notremusique)有可能参加今年的戛纳电影节,这个消息让一同看报的友人们兴奋不已。虽然让-吕克·戈达尔已经是属于电影史上的过去时,早不再是电影热点的核心,但他的电影依然激励着无数做电影的人。就在今年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的索菲亚·科波拉说正是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人的作品鼓舞了自己。一位从巴黎回来的朋友,讲到他看到的一张戈达尔和弗朗索瓦·特吕弗在少年时代的合影,情不自禁地感叹:那是神一样的人物。 前几日在报纸的电影新闻重逢戈达尔,那是从戛纳传来的消息,戈达尔的新作《我们的音乐》(Notremusique)有可能参加今年的戛纳电影节,这个消息让一同看报的友人们兴奋不已。虽然让-吕克·戈达尔已经是属于电影史上的过去时,早不再是电影热点的核心,但他的电影依然激励着无数做电影的人。就在今年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的索菲亚·科波拉说正是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人的作品鼓舞了自己。一位从巴黎回来的朋友,讲到他看到的一张戈达尔和弗朗索瓦·特吕弗在少年时代的合影,情不自禁地感叹:那是神一样的人物。
特吕弗曾以极其尖锐、近乎人身攻击的影评进入电影界,戈达尔说:他是我们攻城的锥。同在《电影手册》做编辑的特吕弗、戈达尔以及一批年轻人,纷纷以自己的处女作开始了一场改变电影史的新浪潮运动。然而成名之后,他们渐渐分道扬镳,20年后戈达尔曾失望得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吕弗会变成原先自己厌恶的人———那个拍摄《四百击》的特吕弗呢?1968年后,极左的《电影手册》花了数年的时间攻击特吕弗的资产阶级倾向,后来《手册》无法存活的时候,依然是特吕弗出钱延续了它的生命。
 1968年,特吕弗和戈达尔曾经组成冲锋队,在电影节期间,共同占领了戛纳的电影宫。不久,两人开始有了分歧:戈达尔说:应当继续放片,但不要观众进来;特吕弗说:不!应该让观众进来,但不要放片。另一种说法是戈达尔主张在电影宫的两间放映室里自由放映影片,对任何人、任何影片都开放;特吕弗则主张放映应在电影院中进行,戛纳电影节必须停止。在我看来这正是他们政治观念和电影理想的不同。很多年以后,戈达尔在看过特吕弗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日以作夜》之后,曾当面置疑他说:为什么这部描述电影拍摄过程的影片,唯独没有导演特吕弗和女主角杰奎琳·贝茜在现实中亲密出入酒店的镜头———这是戈达尔亲眼所见。戈达尔觉得,那样的镜头比特吕弗编造的发生在剧组中的虚假爱情故事要有说服力的多。在得不到特吕弗回答之后,他们彻底的一刀两断了。 1968年,特吕弗和戈达尔曾经组成冲锋队,在电影节期间,共同占领了戛纳的电影宫。不久,两人开始有了分歧:戈达尔说:应当继续放片,但不要观众进来;特吕弗说:不!应该让观众进来,但不要放片。另一种说法是戈达尔主张在电影宫的两间放映室里自由放映影片,对任何人、任何影片都开放;特吕弗则主张放映应在电影院中进行,戛纳电影节必须停止。在我看来这正是他们政治观念和电影理想的不同。很多年以后,戈达尔在看过特吕弗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日以作夜》之后,曾当面置疑他说:为什么这部描述电影拍摄过程的影片,唯独没有导演特吕弗和女主角杰奎琳·贝茜在现实中亲密出入酒店的镜头———这是戈达尔亲眼所见。戈达尔觉得,那样的镜头比特吕弗编造的发生在剧组中的虚假爱情故事要有说服力的多。在得不到特吕弗回答之后,他们彻底的一刀两断了。
1984年,特吕弗离我们而去,去世前他已经成为外国人眼中最重要的法国导演,法国人为他进行了国葬。而这时的戈达尔已经不再承认自己是法国人,远居瑞士。为特吕弗作传的作者找到他,请他写一个序。戈达尔在开头写着:弗朗索瓦死了,而我还活着,但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述说忧伤,而我们的痛苦却一直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