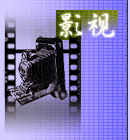一
沙洛扬四兄弟中的两个席柯与毛莫,同另外两个匪徒一道,参与了一起抢劫犯罪。事成之后,席柯与毛莫想要独吞钱财。他俩分手后,席柯就遭到另外两个匪徒的追杀。为了逃过追杀,席柯暂时躲到弟弟爱德华•沙洛扬(已更名为查理•科勒)那里。查理现在是一家街角小酒店的钢琴师。
而他曾经是一位著名的钢琴家。在倒叙中,我们得知,他妻子特蕾莎为了帮助他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不惜出卖自己,满足了剧院经理的非礼要求。事后,特蕾莎感到没有面目再见丈夫。在向爱德华忏悔后,她竟跳楼自杀。爱德华深受刺激,决定隐姓埋名,在一家低级小酒馆弹琴为生。周围的人都叫他查理。
匪徒们跟踪到小酒馆后,绑架了查理及酒店女侍蕾娜。蕾娜暗中爱着查理。在一次聪明的行动中,雷娜与查理摆脱了两个匪徒。
小酒店老板波利诺也喜欢蕾娜,他无法容忍蕾娜与查理的恋情。在一次斗殴中,查理出于自卫杀死了波利诺。为了逃避警察,雷娜驾车将查理送回老家。谁知,那两个匪徒趁机跟踪而至。查理的兄弟们与匪徒展开了枪战。其中一个匪徒向蕾娜开了一枪,蕾娜中弹身亡。
查理又回到了小酒馆,面无表情地弹起了他那老掉牙的旋律。
二
《枪击钢琴师》[Tirex sur le Pianiste,1960]是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1932-1984]的第一部类型片,也是他艺术上最成功、最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品之一。特吕弗从一部美国小说《在那里》[Down There]获得灵感。故事、背景与人物描写基本遵循惊悚片的类型模式。宽泛地讲,影片也忠实于小说本身,尽管特吕弗将背景从美国移到了法国。然而,匪徒的故事很快就变得不重要了,而这个类型的模式与成规也以一种反讽的方式加以处理。事实上,这一故事的大部分情节在影片开始前就已经发生(而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席柯遭到追杀的情形)。其后,这一故事只是断断续续地继续。特吕弗宣称他写的故事有头、有经过、有尾,尽管“我知道,从长远看,我的兴趣在别处,而不是在情节中”。1在《枪击钢琴师》里,他的兴趣在于另一个“故事”,即查理的生活与爱情。然而,这却不是标准的惊悚片的情节,而是特吕弗的电影经常加以探索的人类关系的丰富层面问题了。
然而,《枪击钢琴师》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与20世纪40年代美国好莱坞B级电影的关系。与让-卢克•戈达尔一样(他的早期电影也利用恐怖片材料作为出发点——《筋疲力尽》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电影,正如出演该片男主角的演员贝尔蒙多[Belmondo]在片中故意模仿美国超级巨星鲍嘉[Bogart]的剧照一样),特吕弗也对美国电影着迷。他有一次称《枪击钢琴师》“是对好莱坞B级片的一种尊敬的模仿,我从那些电影中学到了很多。”
《枪击钢琴师》究竟讲了些什么?从视觉上讲,这是一场电影的轮盘赌——黑暗、在阴暗中的表达、城市死角,其中的人物都疲于奔命。从语言上说,它毋宁说是一部喜剧,匪徒们的对话是插浑打科式的,而不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影片中的匪徒更像一群天真的小男孩,而查理对他们的音乐打火机、新的吸水笔、鳄鱼皮带和其他用品同样兴致勃勃。这些都让特吕弗有机会营造出闹剧的气氛。正如艾伦所说,“当一个匪徒以他母亲的名义发誓时,插入了一个老妇人跌得四脚朝天的画面,很难想象别的电影会这样处理。”
特吕弗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枪击钢琴师》背后的理念是要制作一部没有主题的电影,只通过侦探故事的形式,来表达我对光荣、成功、堕落、失败、女人以及爱的全部看法”。4或许该片最令人惊讶的特征是它向前运动的方式,从喜剧到悲剧、从荒诞无稽的匪徒到真刀真枪的实干、从喜剧式的胆怯到杀死查理所爱的两个女人的情节跳跃。影片跟真实体验一样,也是无法预测的——有些时候近于疯狂,有些时候又辛辣无比;唯一确定的就是不断地运动与变化。
特吕弗研究专家因斯朵夫[Annette Insdorf]曾敏锐地指出,如果说匪帮片或“电影的轮盘赌”具有一种密不透风的形式(类型片的成规就像诗歌中的押韵一样严格),那么,《枪击钢琴师》则是一部辉煌的自由诗,它创造自己的形式。它的开头是相当直截了当的:一个男子从一条漆黑的街道上跑来。他撞在了路灯上,摔倒了。一个陌生人将他扶起来,然后不停地跟他谈论他妻子与孩子们的事情,谈论巴黎处女率的高低问题,而在他的故事讲完后,我们的受害人就继续奔跑。那个陌生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是一个偶遇,跟情节没有任何关系,却为本片定下了基调。这是一种捕捉到了经验流动性的相当现实主义一笔,就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人在某一刻出现,然后就永远地消失。回到与诗歌的类比,这不是押韵,而是一种插入语。
三
我在其他场合已较为详尽地说明了特吕弗是如何利用类型片的模式并一一加以颠覆的:从自由改编(原小说背景与重心的转移)到叙事的颠覆(从匪徒的故事到男人主公查理的性格刻画)。这还特别表现在对人物表现的颠覆上(类型片中通常那种强大的男人变成了查理的怯懦与犹豫)。
因斯朵夫则在其关于特吕弗的专著中,饶有兴味地分析特吕弗影片中的查理,与美国喜剧片大师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关系。他甚至说查理就是根据卓别林的名字命名的。我们只需提一下查理的扮演者查尔斯•阿兹诺瓦非常接近夏洛[Charlot,卓别林的银幕形象]。他俩都易受伤害,都有一种嬉笑与哀婉的混合特质。我们不难看到对卓别林的这一读解与任何一部特吕弗电影之间的联系:从《四百击》到《阿黛尔•H的故事》(经过《枪击钢琴师》、《华氏451度》、《野孩子》);所有这些电影都把着眼点放在了其中人物创造他们人格的行为上(安托万通过他的“反社会”经历,阿黛尔•雨果通过她的日记),或者,对试图塑造他们的人们所做出的反应上(查理与特蕾莎和蕾娜,《华氏451度》中的蒙太格)。跟夏洛一样,特吕弗的人物总是游离者,只能暂时控制他们进入的世界——例如在恋爱的时候——却是绝对的无力与孤独。他们交织着精力与痛苦、胜利与失败。《枪击钢琴师》中的查理是特吕弗式男主角的一个动人例子,他介于浪子(低级酒吧间的钢琴师查理)与世界上最著名的人(音乐会钢琴家爱德华•沙洛扬)之间。在电影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分裂的人:他哥哥叫他爱德华,但是他却要他像别人一样叫他查理。这种外部世界的分裂折射出他内心世界的分裂:我们经常从这部电影的音轨中听到他的内心独白,却跟他外在的行为相冲突。当他跟雷娜走在一起的时候,这一点得到了辛辣的展示。他痛苦地自我折磨:“要不要握住蕾娜的手?”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他紧紧地握住自己的拳头。而当他终于鼓足勇气邀请她时,她早已离去了。
查理的腼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向蕾娜表达得太晚了,更为可悲的是,在倒叙中,他向特蕾莎的表达也是太晚了。正如艾伦所描述的那样,特蕾莎的忏悔以一阵不详的沉默开始,摄影机在妻子与丈夫之间做交叉剪接,而当特蕾莎细述她为了查理未来的发展而牺牲自己时,摄影机从一张脸摇到另一张脸。查理痛苦的内心独白反映了他自己的两难:事实上他必须安慰特蕾莎,但是又做不到,他走开,犹豫了半天,才又回来。音乐的节奏逐渐加强,摄影机快速地掠过查理,进入房间,到阳台上,然后突然往下降,在下面的人行道上出现了特蕾莎的尸体。
在这里,特吕弗展示了人格是如何依赖于时间这一点的精辟见解。重要的与其说是我们做了什么,还不如说是我们是在何时做的。物质环境较之心理运动是处于第二位的:“我知道这有点儿怪异,但是我不喜欢风景或是事物。我喜欢人们;我对人们的观念与感情感兴趣。”在特吕弗的影片中有一种暗示,人们可以选择他们的空间;人物与车辆总是在不断的运动中,但却得到时间的控制与界定(考虑一下《柔肤》中那个狂热的开始场景)。他们朝哪里走并不重要(皮埃尔与尼柯莱逃离巴黎后有什么不同吗?),因为他们的内心风景总是行李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他们运用时间是否恰到好处:在《朱尔与吉姆》里,卡特琳娜与吉姆之间的信件总是交叉而过;而《柔肤》的结尾则充满了暴力色彩,仅仅因为皮埃尔的电话迟了一分钟,他就被暴怒的法兰卡枪杀了。
对查理来说,行动与意图总不能一块儿到来——除非是在他演奏他那首老曲子的时候。在他的音乐中,时间是给定的,空间则充满了有节奏的停顿。但是当他与人们交往的时候,他却错过了许多节奏。富有意义的例外只有一次,即当他跟妓女克拉丽莎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相处简简单单,这一点又因为他们在上床嬉闹前那节拍器可预测的节奏而得到强调。在另一个场景中,他无法鼓起勇气去按剧院经理的门铃,只有当一个女人开门出来后才能进去。这个场面表明了特吕弗利用优柔寡断的时刻的方法,它迫使我们去体验人物经验时间的方式。查理曾想对他的老板波利诺友善些,结果却在自卫中杀死了他。他爱着特蕾莎与蕾娜,对她俩的死却负有间接的责任。
在一篇题为《透过镜子》[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的著名论文中,罗杰•格林斯潘[Roger Greenspun]帮助我们看到,特吕弗为查理的人格分裂创造了一种风格的类似物。尽管《枪击钢琴师》表面上没有什么结构,这部影片却密不透风地建立在相应行为与镜像反射之上的,这也暗示了生活不断地自我重复。影片的外部结构通过查理与女侍者蕾娜的爱情故事加以呈现。其内在结构却是通过爱德华(即查理)与特蕾莎(也是个女侍者)的爱情故事的闪回来进行的。外在结构中的第三个角色是波利诺,他对查理的姑娘蕾娜的兴趣,对应于内在结构中的剧院老板施梅尔对爱德华的妻子特蕾莎的兴趣。这两个男人都给了查理一份工作,两人都知道他的弱点(恐惧与胆怯)。爱德华遗弃了特蕾莎是因为她已经成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被玷污了的、肮脏的抹布;而他冲过去捍卫蕾娜正是因为波利诺骂蕾娜被玷污了(这也指向了查理与波利诺在他们对女人的极端观点之间的相似性)。特蕾莎跃入了一片黑暗的死谷,而蕾娜却倒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格林斯潘还认为,在过去,我们都有“一种关于献身的爱,以及由黑暗的交易支撑着的辉煌成功的罗曼蒂克的故事”,而现在,却是“一个由无可救药的浪漫之梦所照亮的隐晦而又肮脏生活的故事。”
四
《枪击钢琴师》既利用惊悚片的类型成规,同时也颠覆了类型片的成规。最明显的一种颠覆形式出现在特吕弗对悬念的处理中。惊悚片的一个重要成份是制造悬念,激发好奇心,从头至尾吊观众的胃口,想要知道“结果怎样”以及“是谁干的”。而特吕弗及其导师希区柯克对“是谁干的”这一点都没有什么兴趣。特吕弗曾经这么说:
特吕弗:围绕悬念这个词有许多误解。你在自己的采访谈话中多次解释道:悬念不可同惊栗混为一淡。现在我和你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有不少人仍认为,有悬念即有恐吓效果,两者息息相关……
希区柯克:绝不是这回事。……你别忘记,对我来说,神秘往往不包含悬念。例如在Whodnit(推理小说或神秘小说)里,悬念是不存在的,而只有一种知性上的疑问。所以它只能引起一种缺乏激情的好奇;而激情正是悬念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激情就是害怕,就是为某人担忧,而这种恐惧的强弱取决于观众和处于危险中的人物认同的深浅程度。
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喜欢在一个镜头或一场戏中创造并维持悬念。(却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要将秘密保持到故事最后)他俩都将悬念与强烈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枪击钢琴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幕,查理鼓足勇气想邀请蕾娜一同喝一杯。这个场面的安排让观众禁不住要问“下面将发生什么”?这一兴趣通过一个相当复杂的情感之网得到维持:不知道查理能否克服他那种长期形成的羞怯症,不明白蕾娜的心理状态(由于缺乏进入她的内心的手段:视角是查理的,画外音也是查理的)。如此相当巧妙地调控观众的情绪后,特吕弗开玩笑地让这一悬念蒸发了:当查理终于鼓起勇气想去抓住蕾娜的手时,她早已消失不见了!
《枪击钢琴师》颠覆类型片模式的最后一个地方在于将电影本身的主题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正如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的那样,这部影片只在外表上是惊悚片。实际上它是对异性关系的复杂领域所作的探索,更是对电影,特别是法国电影的一种陈述。影片的自我指涉通过许多手段加以表达。最初的暗示始于影片的开头,当观众早已对它的突然变调感到震惊时,它还让观众意识到了摄影机的独立性。当席柯离开那个持花的陌生人后,他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原先正在被追逐,于是又向黑暗中逃窜。这时摄影机暂时找不到他的人影,只得晃回来,然后再找到他。这一小小晃动的意义要比它在银幕上出现的不到一秒钟的空白大得多。它代表了叙事的中断,是一次故意打岔,向观众抛眼风,告诉观众:情节是虚构的,是胶片,是电影。
五
作为新浪潮电影最杰出的成果之一,《枪击钢琴师》乃是法国这一伟大的电影运动的界定性标志。这一点特别表现在这一运动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上。巴赞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电影的紧密关系,似乎象征了这两个电影运动之间的联系。法国批评家和电影制作者们与他们的意大利导师们拥有相似的东西:他们年轻、独立、没有工作室,他们采取现景拍摄法,起用非职业的或不知名的演员,诉诸日常经验。这些痕迹导致了那些最能标志着新浪潮的东西:自发性和即兴性。
因斯朵夫分析了法国新浪潮电影与美国新爵士乐运动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是丰富而又深刻的,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叙事与旋律之间的相似性的话。两者都有一些人们可以进入其中的东西,因为它们都讲述“故事”;它们都有内容。但是,由于新浪潮与新爵士乐都植根于自发性与即兴发挥,对它们的处理就成为经验的一个有机的部分。有趣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爵士乐大师加莱特[Keith Jarrett]与特吕弗都转向了更为“古典”的趋势。两人都是通过节奏——视觉的节奏(蒙太奇)与听觉的节奏(打击乐),以及丰富主题的肌理,迫使观众从情感上去体验他们的艺术。音乐中的“人物”是乐器(正如电影中的角色,需要演员赋予他们以生命),而故事则只有通过这些个人来加以表达。通过演出者的中介,乐器与人物都有台词要说。
尽管法国新浪潮与美国新爵士乐都有其自由和即兴发挥,以及实验性的一面,两者却都尊重传统;特吕弗和加莱特既是创新者,也是总结者。与新浪潮电影年轻有为、第一流以及好冲动的态度不可分割的是,他们对电影史的清晰意识,这已经成了一种十分紧张的电影自我意识。《枪击钢琴师》是一位电影爱好者的作品。它在调子上的突然转移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观看一部电影;一个最令人开心的例子是大胆的插入,当其中一个匪徒发誓的时候:“要是我撒谎的话,让我妈妈摔死好了”,我们就突然看到一个老妇人摔倒在地。因此,自我反思的品质在新浪潮电影丰富的暗示性中成了最引人注目的东西。有些观众感到这些自我指涉是只有精英们才能理解的幽默;更到位的说法是文森特•凯恩比[Vincent Canby]的印象:“引语总是与特吕弗以表面上如此轻松地制作的影片那种多层次结构相关。但是,它们对它所提供的最主要的愉悦来说并非本质的东西,而是额外的津贴”。它们事实上是向传统、向形成新浪潮感觉的导演与电影致敬的做法。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艾伦对《枪击钢琴师》的评介:“就整个调子来说,特吕弗爱他所钟爱的好莱坞B级片,并且从容不迫地表现出来。它也许会在新浪潮的历史上大受赞赏,拿来跟戈达尔的《筋疲力尽》互比是恰当的。两者都类似通俗剧,兼具诙谐与罗曼史,此外还有脱离常规、超乎想象的神来之笔。《枪击钢琴师》的整体效果是由前所未见的类型与气氛混合而成的,其内在精神无从捉摸,却又充沛跃然,这使它成为不凡的当代巨作。”他接着说:查理回到酒馆的钢琴前,弹奏出令人难忘的主题曲。他空洞、哀伤的定格伴随着逐渐加强的音乐,摧毁了片头那个琴键的镜头。一切又回到起始。酒馆又来了个新的女侍;但是查理的孤独却毋庸置疑,他仍是那个虚无的钢琴师(不过,疑问成了:他是否还会害死这个新来的女侍?)。这部影片显见的魅力之处,是在每个可能的困境中找出新的方向,一直持续到片尾。这种处理震惊了(或误导了)观众。这部片子和特吕弗其他影片的区别,就像《偷吻》一样,片中的主要结构事实上都是随兴地任其“发生”。但那些不可预料的“气氛”转移,却赋予了《枪击钢琴师》不可捉摸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