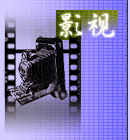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现在还有《花样年华》的碟卖吗?”春节后第一次在家里招待朋友。
“有。想看了?”
“恩,前段日子满大街都是,却没有买。”
“是不是听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曼玉和梁朝伟唱的歌,就想看了?”
我笑了笑:“是的”,顺手关了火锅。
“不过电影里面没有他们唱的那首歌。”
“没关系,帮我找找吧。”
假日晚上的大花落地窗帘宁静安谧,有点做作的温馨。歌儿里唱:“——都怪这花样年华太美丽……”
“那张碟买到了,有空给你。”
“好。”
影碟在柜子上睡了两天。
“张曼玉的皮肤真好。”我看着封套。
“那是做出来的效果。”
“她有多大岁数了?”
“总有四十来岁了吧。”
“真看不出!”
“这个片子很闷的,节奏特别慢。”
“看看再说吧。”
如其所言,片子开头是没有声音的。只有红色底子的字幕,一页页打出来,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有了声音时,却不是音乐。
细密的上海话,正适于陈述细碎的尘世生活、窄窄的房子里搬家的杂乱声音,张曼玉精致的面孔、婉转玲珑的旗袍身材、和笑容。走廊里与梁朝伟的一瞥,不经意地成为了邻居,屏幕外的我,俗气地知道故事将由此开始。
“侬要去接先生的飞机?”家常的上海女子方言。
“是呵。”婉娩清晰的声音,窄窄条纹旗袍的背影走出视线,在浓漫着世俗生活气氛的麻将牌声中,音乐,突然意外地就来了,拉开观众与画面之间的距离,在红尘琐事与我们的注视之间,隔出一层迷离的雾气。
低低压抑的鼓声、齐齐促促地拨弦,狐步节奏,清晰的小提琴从幕布后渗透出来,保留了本质的悠扬、浸润着不相干的忧伤,好象一个场外诗人决心闭紧了感性的双唇,用冷静的眼眸看着这个情感的场景里发生的、不可能是喜剧的故事。
当同样的音乐主题第二次出现时,又是走廊的相逢,在深了一寸的注视里,有着各自心照不宣的落寞。厮守家庭的感情已经出现倾覆,错不是她的、也不是他的,一直没有露面的那两个人,他们又是怎样开始的呢?这已经不重要,在绮靡缠绵的音乐第一次响起时,茶餐厅里关于皮包和领带的对话,揭开了故事的最后一层序幕。
我想王家卫一定有细长柔韧的手指,他能够把一块积木解剖得纹理纵横、结构清晰。整个片子的结构和意想简直象程序及函数那样明晰。每一步情节的展开都是一个嵌套,穿插着规范的意想,格子、条纹的、大花的,以及最后色彩暗淡的旗袍,欲抑时的条纹、欲扬时的花朵。所有的情节和画面都在对应着展开,而主题音乐则在其中充当引导的使者,步步入深,每一次出现都是一个新的情节、新的心情层面。
两个主人公的身后,是两个并邻得仿佛孪生的家庭,各自的伴侣在张扬的欲望里苟合,把我们的两个主人公推到了台前,在灯光里突兀又尴尬地相望。暗淡的背景里,梁朝伟只用眼神,便深入了所有的情节,而张曼玉的面孔则如白瓷一般精致、落寞……
而在主人公各自的眼前,世俗情景也是那样缤纷张扬着的--在情人和太太之间游刃有余的老板、借钱买马嫖妓的朋友、通宵的麻将、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的厨房……在所有的不加抑制的张扬中间,只有他俩,用紧锁的面孔和脚步在黯淡的巷子和暧昧的灯光里迟迟艾艾地拖沓着将要发生的情节、踯躅地一遍遍排演着各自那位偷情的情节,她的手指在他的领带下端轻轻一拨,轻佻、风情,象门缝里的偷窥,却是假的。
一个欲望飞扬的场景里发生着一个大家都知道将会发生的故事,音乐和色彩留足了画面的飞白,主人公却划出一道枯笔,王家卫捏着手里的橡皮泥就象捏着观众的心,一收一放。只有他,让偷情都偷得那么不畅快。
不是自己的的高跟鞋夹着脚、却要自己匆匆地揉,食不下咽的糯米鸡、惊恐地跑回自己的房间。孙太太的面孔是社会规范的要求,却对应着佣人的热情那么质朴。厨房里假装不经意地做了一锅芝麻糊,要盛出的也只是那一碗。再进厨房时,是为了房东太太的话,安心、收心地与房东家一起吃荠菜馄饨,她的眼睛如此忧伤迷离,微微开着旗袍领口的扣子,接着的镜头切到了他身上,同事中间、谈笑风生,却有着同样固执的落寞的眼神,松开领扣的白衬衣、投向镜头同样的视线……
片子里的意想如同森林里的猴头菇,对应地生长着,这边有一枚,那边必然也会交代出一颗,从服装到音乐,从天气到水声,从墙壁的灯光到一个小小暧昧的绣花拖鞋。王家卫用清晰的思维构造着一个世俗简单的故事,犹如巴赫的赋格所富有的建筑美。他从生活的面粉里揉搓出面筋一样柔软精确的情节,再把她们捏成对应的形状填塞在一格格钢筋中间,大手一挥,这样感性的电影便从此有了结构的力量。
主题音乐再次响起,是在旅馆的走廊,地板上走过他如风的脚步、她飘满花朵的旗袍和欲望的红大衣。匆匆赶来、她在走廊的楼梯扶手上靠了靠,打点起一副心情。音乐里,她说:“我们是不会和他们一样的。”
就这样自欺欺人地打上格子、定了性。却在夜晚阴暗潮湿的窄巷里一寸寸掐过手臂的肌肤,哭吗?第一次是先生,在浴室的水声里压抑着哭声,这次是他,在雨后的水声里哽咽、而至伤心大哭,谁还能说这只是分手的排演。是爱吗?是家吗?岁月如水,花已非花,自己却始终是自己的了。雨后的铁栅栏黝黑潮湿,迷离的花影儿呵,摇曳在坚硬的栏杆中间。
在周璇清澈绮丽、弥漫着无知的忧伤的歌儿里,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跟我走吗?会吗?会吗……所有的痛苦、欢乐和寂寞都只能自己承受的花样年华呵。
热带的孤树独立在傍晚的天空下,男歌者靡靡沙哑的声音、旋律里有着热带的疲惫、宛转和无力。灯光散漫的四壁,眼睛铭记着这情景、手指抚摩着他的痕迹,打开那盒香烟,深深嗅着。电话铃响了,却没有说话……真的要记忆吗,还有必要么?导演在捉弄人呢,在影院里,我们的喜怒哀乐不过是他手中的橡皮泥。
张曼玉无辜地忍着眼泪与精明的房东太太交谈。王家卫恶作剧地让她带着一个“满可爱的小孩子”住在旧房子里,又让她与沉溺在旧日情怀中的他再次错过。从顾家与孙家的窗子望去,都有明丽的花朵开放在铁栏杆里。
六十年代底香港的动乱、柬埔寨的政治新闻录象,这些都不过是导演手里的铺纸,他要给我们看的只是一个如此细碎卑微的故事,淡然悲悯的低音提琴里,一个穿着黄袍的小和尚无知无识地看着他把心事吐露在粗糙的树洞里,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段花样年华,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尾声:
多余的字幕在最后再次出现,一派旧红的底子,同样的主题音乐里打出冗长的演职员表。散场了,音乐陪伴你走出影院,这样的故事在电影院以外随时发生着,感喟着每个人都有的花样年华。
如果你肯坐着,一直等到最后。当字幕上出现鸣谢的公司单位和音乐目录时,声音就变了,在脱离了靡靡无力之后,在寞寞的大提琴和清澈明晰的拨弦中间,导演和编剧向留下的人投来一缕冷静、狡黠的目光,告诉我们说这不过是他们编造的一个精致的故事,所有的缺憾和缠绵,都只是这块积木的纹理。这,便是人们所谓的花、样、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