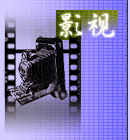历经了五十年代朦胧式的无奈,六十年代宣泄式的反叛,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年已经厌倦了流浪的孤途。在孤独与迷茫中,他们开始寻求灵魂的回归之路:回归主流社会。马丁·斯科西斯的《出租车司机》塑造的正是这样一条回归之路,还有那在路尽头死去的独语者。
对主流社会的回归意味着不再孤独。可在路上的主人公特拉维斯仍然是一个喃喃自问的独语者,他仍然孤独。
路上的一切——环境——没有预现出一丝回归后的温馨,“而是作为人物的对立面出现:无论是28号大街,还是8号街区,以及主人公的住所、妓院,都笼罩在黑暗中。夜色中,纽约显得光怪陆离。灯光下,闪烁着团团毒气,雨水使纽约的街道变形,来往的汽车灯摇曳不定,像鬼火一样跳动。黄色的出租车似幽灵般穿梭在由红色斑制造出来的丛林般的街道,驶向远方的夜雾中。妓院的长廊里点着几盏灯,周围和前方是黑暗。黑色的区域像一块沉重的铅块,每一道黑门都是一个危险源,充满了神秘而不可测的气氛”。
特拉维斯的孤独,源于他的清醒,他虽置身如此环境却仍保持着的清醒。影片以贝丝和艾莉斯分别代表社会上层和下层作为对照,她们与特拉维斯处于同一环境,却没有特拉维斯孤独者的感受。路尽头的主流社会不需要这种清醒,路另一端的非主流社会同样不需要。而特拉维斯在路上。回归必须化清醒为麻木,接受并融入这个环境,路上的特拉维斯还没有。
这种孤独感以及人物与环境的对立,在斯科西斯的影像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首先,影片以夜景为主,以黑色为主基调,以路灯和车灯为主光源;镜头跟随着出租车在夜晚的纽约大街上游动,在大面积的黑色块中,夹杂着闪烁的路灯、幽灵般滑过的车灯。在光影中营造出如此环境如此氛围的同时,影片加入特拉维斯无奈而失落的画外音,很好地衬托出主人公那渗入骨髓的孤独情绪。
其次,影片充分利用了前后景的场面调度,往往以街道、车流、行人为背景,以特拉维斯和他的出租车为前景,前后景截然分开。纽约污秽迷离的环境,大部分是在出租车里这样一个封闭的视点透过车玻璃窗被拍摄下来的。在这样的景深画面中,我们能感受到独语者在如此环境中的孤独与凄迷。
与现实环境的对立标示了路上的特拉维斯独语者的身份,而对独语者独有的那份孤独的厌倦甚至恐惧促使他继续选择回归,哪怕那里也并不温馨,有的只是无尽的肮脏。这时候的特拉维斯是一个行动者,他必须用一系列的行动来催动自己孤独的脚步以离开孤独。影片为他每一次的行动都配备了一个行为对象:
贝丝
作为总统竞选人帕兰汀身边的工作人员,贝丝是绝对主流社会的代表。这正是特拉维斯选她作为第一个行为对象的心理原因——贝丝的身份契合了特拉维斯向主流回归的方向。可也正是贝丝的这一身份定位,注定了特拉维斯努力的终归失败——他们属于不同的两个世界。
可幸的是,贝丝虽身处主流,却“并不快乐,需要一个朋友”——这是那个以上述环境为表象的主流社会的特征所必然引发的——而这点与特拉维斯的孤独更是契合的,这为他们感情的短暂存在提供了可能。
在这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影片其实是在进行情节的延宕和情绪的积累,“这是进步的矛盾”。
艾莉斯
作为一个妓女,艾莉斯是与特拉维斯比较接近的,是非主流的社会遗弃者。不同的是,后者已开始向主流靠近,而前者却仍沉浸在那栋漆黑神秘的大楼中而不自觉。而这一不同点正是特拉维斯接近艾莉斯的动机所在:经由与贝丝——主流——的由合而分的他已向主流前进了一步,俨然已经站在主流的立场上,试图拯救处于“堕落”之中的艾莉斯。
特拉维斯这种超前的自我角色定位,其实还只是一次排演,严格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而他的努力终归还要失败。
可这还是“进步的矛盾”,失败的背后是悄然的积累与前行。
帕兰汀
这种积累只表现在叙事上,而特拉维斯是不自知的。当他发现自己的一次次努力——不论是对上(贝丝)的亲近还是对下(艾莉斯)的拯救——终归都是失败而找不到出路时,他必然要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宣泄内心的不被理解和恐惧,并且证明自己对主流的价值。于是,他决定暗杀总统竞选人帕兰汀。这时的帕兰汀在他心里已不是主流社会的统治者,而是主流的破坏者。因此,此时的特拉维斯甚至已把自己放在主流社会的卫士这一位置上——他对艾莉斯宣称自己在帮政府办事(指暗杀帕兰汀)。
特拉维斯这种荒唐的一相情愿以及力量对比的悬殊,造成他在行动中还没来得及掏出枪就只能逃之夭夭。但借此影片情节和情绪的积累却已达到将发未发的充溢状态。
斯波
这时特拉维斯的心态已经无法平息下来,一场爆发已经成为必然。于是,他又只能把目光从上层(帕兰汀)移向下层(斯波),并开枪打死了“市井流氓”斯波、妓院里看房的老头和一个嫖客。
结果是,首先,他终于拯救了艾莉斯,使艾莉斯由一个妓女重新成为一个学生,从非主流彻底走向了主流。不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已是对特拉维斯的主流身份的一次承认和肯定。
其次,特拉维斯终于走完了自己回家的路,达成了自身对主流社会的回归,摆脱了长期的内心孤独。报纸上“出租车司机与黑社会枪战”的主流话语正是这一完成的标志。
这时,那个经常自我呢喃的独语者特拉维斯已经死了,蜕变成社会主流类群中的一个。特拉维斯不再孤独:艾莉斯的父母给他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贝丝对他也不似以前冷酷了。
或许他真的已经摆脱孤独,可那个污秽阴森的现实环境还是没有变。或许他还是厌恶那里的街道,回归也只是他因对孤独的恐惧而作出的无奈选择。
如此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或许斯科西斯也无能为力。
我不禁想起何其芳的一段话:
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或者狂暴的独语。
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
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
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