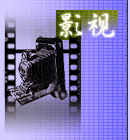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
麦克默非戴着灰绒帽第一次走进疯人院,朝警察作鬼脸的时候,无疑低估了这座铁丝网密织的集中营的强制力。即便他一次次搞恶作剧,把护士、医生、保安搅得鸡飞狗跳,但最终发现这里并不是一个乐园,或者说这里是一个乐园的想法只是一种短暂的幻觉。
拳头、粗壮的胳膊、镇定药、电流,镇压了一波波”暴动”,如果拉其德护士认为这个词合适的话。一些个颇具特点的臣民向暴君发起挑战,暴君不是这座疯人院里领薪水的任何一个人,要知道,即便麦克默非一举掐死了护士,即便杰夫砸开窗户后一帮兄弟鱼贯而出,他们依然没有摆脱暴君的统治。我注意到片尾杰夫那个僵硬的奔跑姿态,他奔向了森林——没有人类的地方,歧视、偏见、野蛮、暴力荡然无存,印第安人的天堂。
他们是一群“病人”,这是拉其德护士反复强调的话。我注意到她一贯的表情,没有微笑,是的,你无法对一些貌似人类的怪物微笑,你需要的只是秩序、有条不紊、温顺的绵羊,每一个人都恐惧触碰高压线,惩罚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实施。
他们是一个反面,被残暴地推到了“正常人”的反面,于是他们失去了自由、尊严以及正当防卫的权利,他们甚至无法受到怜悯,无法为自己申辩,他们仅有的权利也许是每天围起来向护士提一些永远无法满足的要求。
疯人院是一个独立王国,拥有完整的暴力机构:警察、军队、高墙、审判者、监狱、行刑房。这里也有虚伪的民主,9:9or10:8的问题使得麦克默非天真地像个孩子,其实这里的每一个“病人”都是天真无邪的孩子,切丝、马蒂尼、哈丁……他们可以大声地哭、笑、闹,只由于他们是一群心灵还未被工业社会的文明法则所禁锢的人。比利的结结巴巴使得他在对姑娘表达爱意时困难重重,却丝毫无损他被兄弟们敲锣打鼓推进一夜春宵时的那份激动。
“正常人”无法想象在一个冰冷的建筑里,在护士的铁面和保安的铁拳下,一群被编上了号码的人如何上演他们的“狂欢夜”。诸神退隐,一班最脆弱最无助的人的肆意狂欢,是整部电影里最激动人心的画面。在巴赫金眼里,狂欢是一种未被认知的、激越的生命意识,其产生于民间底层之中。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因描绘了文革的非人年代里男女青年之间汪洋恣意的情爱世界而被誉为“狂欢文学”,那么在疯人院中种种歧视和管制之下,麦克默非的“出位”之举则算得上是银幕里的底层狂欢吧。
整部电影是一出所谓“正常人”对“癫狂者”的压迫悲剧。那么何谓癫狂呢?福柯在其《癫狂与文明》一书中指出疯癫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产生的效应。癫狂是被理性——这一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奉若神明的价值——所强加的罪名,人们恐惧非理性的东西,就力图把这些东西打入“精神病院”这样的发明中。看看尼采吧,这位最著名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背负的“疯子”的称呼与“天才”一样世人皆知。可问题是,理性凭借什么具有这样至高无上的地位? “病人” 切丝由于自己的烟被缴走而撕心裂肺的非理性哭喊与护士拉其德无动于衷的理性麻木相比,何者更可以声称代表人类呢?这让我想到麦克默非说的一句话:那些在大街上行走的人要比他们这些关在疯人院里的病人更加病态。与其说这句话是讲给拉其德护士听的,不如说是讲给我这样抱着多少有些不屑的心态观赏“疯子”们的“丑态”表演的人听的。或许我们每一个观众可以扪心自问,我们的对于所谓的“他者”的优越感是否也有着病态的毒素呢?被法则、花样翻新的教条、恐惧、暴力所挟持的人类文明是否应该反思其自身的种种问题呢?麦克默非和杰夫所期盼飞越的东西难道仅仅是疯人院吗?
麦克默非,一个牺牲品,比利也是,还有其他人,只有杰夫,这个用装聋作哑来抵抗这一切的印第安人回到了自然的宁静当中。可是,那些看着杰夫逃走的“病友”为什么甘愿选择留下来?惰性?还是麻木?那么人类呢?是否也是那只在锅里等着水慢慢煮沸的青蛙呢?
牌局在继续,相同的四个人,四个座位,影片的开头及结尾处展现了同样的场景,唯一不同的是本来鲜活乱跳的麦克默非已经被折磨得不醒人事,疯人院里唯一的一缕黑色叛逆被无边无际的白色所吞噬。打牌的人依旧打牌,疯人院依旧戒备森严,那些自愿留在那里的人依旧有滋有味地过着非人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将如何面对这种尴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