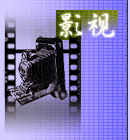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老师说上帝是不可见的,无所不在,你能感受到,你用指尖了解,现在我不停的伸出手,直到有一天我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为止,告诉每件事,甚至是我内心的秘密。”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曾经想过自己是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
我时常会想做一个说不了话的人,用手势取代一切的语言。在寂静的空间里,只能感觉到时间的缓缓流动,手指像蝴蝶一般在空中舞动,那些呆头呆脑的文字变的充满了思想,似乎可以代替语言讲话,在我和与我交谈的人之间。如果所有的感情都可以从指尖流露,思想像火花一般在空中碰撞,发出星子般的璀璨,应该是件很美丽的事情,而且要比从嘴里说出来真实许多。
各种残疾里面最残忍的莫过于看不见东西,看起来和常人无异的一双眼,却是空洞的没有一丝内容,纵然是最灿烂的光线也穿不透。我曾经试过闭着眼睛走在路边的盲道上,就是那种竖直表示直线行走原点表示拐弯或是道路的终结的道路,我无法控制好身体的平衡,脚下的不平坦使我接近于东倒西歪,尽管盲道的高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也试过在空无一人的笔直路上闭起眼睛,却怎么也迈不出第一步;同样我还试过拉住某人的手闭起眼睛走路,却一样的踌躇不前,这和信任无关,而是与生惧来的一种对黑暗的恐惧,四肢仿佛都浮在了空中,相互间没了关联,我惊慌的舞动双手,明明知道前方什么也没有却始终挣扎着想要抓住一些东西。
于是我理解了《天堂的颜色》(the color of paradise)里的盲童穆罕默德在试探着去触摸每一双伸到他面前的手时心底的感觉,从老师手中传递的信任,从祖母的手中握住的爱,从妹妹手中牵住的亲情,而面对迟来的父亲,穆罕默德试探着去找他的手,心底由期待、怀疑、忐忑、猜测搭建起的防线终于在触到父亲结结实实的手的那一刻全盘塌陷,短短的探寻-接触的过程里,他“经历了一生的煎熬”。来自不同人的手对于他来说有着不同的温度,不同的质感,在不同的时刻传达着不同的讯息,对于一个看不见的人而言,手的触感成为了每个他遇见的人的“脸”(标记)。
只是我的手,在我闭起眼睛摸索的时候,却是盲目的在空中比划,毫无灵性可言,因为它们已经习惯了被眼睛指引,做眼睛的奴隶。
当我在阳光下闭起双眼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橙黄色太阳的温度,用手在眼前划出弧线,感觉就像一只黑色的蝴蝶在振翅。盲人却是不可能有光感,世界在他们眼中是无止境的黑暗。我相信影片中老师所讲的话,上帝是疼爱瞎子的,因为“感知”比“视觉”更为真实;在关上了他们的窗口后,一定在另外的地方另辟巧径。因此,盲人有最敏感的触觉和最透明的心灵,语言可以欺骗,手的感觉却绝对真实,他们是真正用指尖在触摸这个世界,一寸一寸的;同样,声响成为辨识世界的另一只“手”,所有能看见到的事物都有着自己的呼吸,然而常人却只懂得去看,而忽略了聆听。
《天堂的颜色》以长达数分钟的黑暗作为开篇,充斥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声响,它们是盲童学校里的孩子们用来辨别属于自己东西的方式。这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眼睛,因为功能的退化而变的形状丑陋甚至吓人。当他们睁着毫无感觉的眼睛在“凝视”什么的时候,也许就是和上帝做着对话。对比鲜明的,是他们的双手,在书写盲文时难以想象的灵巧,并不亚于钢琴家在黑白世界里飞舞的双指。
这是盲童学校孩子们回家的日子,穆罕默德在等待父亲的到来。然后父亲却另有打算,妻子的早逝和家庭的压力使他为自己寻觅了另外一位伴侣,眼盲的穆罕默德成了这场即将到来的婚姻中唯一的阻碍。满怀希望的穆罕默德在学校里等待父亲的到来,却不知道几步之外的父亲正一脸阴郁的看着自己。父亲并不想带穆罕默德回家,却不能破坏老师口中“勤劳工作的好父亲”的形象。
在路上,穆罕默德贪婪的用手指,用耳朵去感知一切回家的喜悦。手指划过窗外的风、划过小溪底的石子、划过路边盛开的花,聆听着鸟儿的叫声、水的流动。
穆罕默德的回家得到了祖母和妹妹们的热烈欢迎,他的盲文读书更是得到了老师和孩子们的称赞。另外一边父亲也在紧张的计划着自己的婚礼,最终不顾祖母的阻拦把穆罕默德送到了远离家的木匠处。
祖母在寻找穆罕默德的途中染病而死去,父亲的婚事也因为这一系列的“不祥之兆”宣告结束,心灰意冷的父亲在接穆罕默德回家的途中遭遇了河水爆涨,儿子随着断桥被卷入水中。盘亘在父亲心中不为人知的阴谋终于借助自然的灾难得以实现,看着儿子的手挣扎着淹没在汹涌的水中,父亲跃入水中寻找,最终在沙滩上找到了毫无知觉的穆罕默德。在父亲的眼泪中,天堂的一束光直直的打在穆罕默德的手上,这双感知上帝、触摸世界、辛苦的找寻爱的手,恢复了一丝的颤动。
色彩的绚烂和各种声音的运用是电影比较突出的部分。世界对于穆罕默德而言是一片永恒的黑暗,然而葱郁如画的田野,明媚的衣衫以及四处盛开的鲜花反映出他绚烂的内心世界,这是穆罕默德心中天堂的颜色,也是爱的颜色;对于自然界各种音响的运用更是贯穿影片的始终,如果不看画面而单单捕捉声音,这俨然是一部生趣的“自然世界”。
只是在影片的结尾处,导演也许是想借父亲的醒悟来安慰穆罕默德被伤害的心灵,我却很难认为父亲最终的寻找是出于良心的回归,我始终相信那仅仅是一种本能的自责。主观的阴暗愿望恰巧借助外物而实现,于是无补的结果扣上愧疚的帽子总是能让自己心安。然而上帝最终是回应了穆罕默德,如果说有什么光线可以穿破盲人的黑暗的话,那只能是来自天堂的金色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