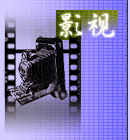试图用手来辨别一头大象的盲人是不可能准确地描绘出大象的全部轮廓,每个盲人根据自己接触到的部位所描绘的是彼此不同的存在,这是公元前2年印度佛经里的一则寓言故事,指面对同一个事物,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而实际上每个人都仅仅看到了事物的一部分——每个人自己那部分。 ¬¬加斯•范•桑特2003年新片《大象》取材于1999年震惊全美的哥伦拜恩中学枪杀案,片名来自英国导演阿兰.克拉克(Alan Clark)1990年的遗作《大象》,其含义则来自上面这则家喻户晓的古代寓言。不管是扮演一个盲眼的观众,还是充当组织一场“摸象仪式”的法师,加斯.范.桑特想在不让观众变成盲人的情况下,用我们的双手来摸索并再现这头“大象”。
就在1999年“哥伦拜恩惨案”发生的那个礼拜,加斯在看了传媒的报道后,联想到1990年阿兰•克拉克为BBC电视台指导的影片《象》,加斯就产生了拍摄这部电影的想法。克拉克的《象》讲述一起发生在北爱尔兰的连环凶杀案,围绕这起凶杀案,媒体和警方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大家莫衷一是,不知道该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哥伦拜恩惨案”发生后,媒体过度渲染其血腥场面,很多记者、犯罪专家、心理学家和青少年问题研究者大加分析和评论,围绕这起少年惨剧周围的是各种猜测、无端的责备,同时也变成公众的一种消遣。这一切都令加斯感到反感,加斯认为这是“美国新闻史上的一次丑闻”,他说,“在这个时候,只有拍一部电影才能再现整个事件的真相”。当他找到一些电影公司和电视台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很多人迫于当时当事人家长和媒体之间的法律纠纷以及舆论的压力而辞决了他。事隔三年,终于HBO电视台同意投资拍这部电影。
与2002年的《黑枪事件》不同,加斯•范•桑特的《大象》是一部概念性极强的电影,他力图通过“纯粹客观”的电影方式再现整个事件的过程,而不是自己或者他人的主观判断。根据真人真事改变的电影在美国并不少见,或以主人公命运张力作为情感基调(索德伯格的《永不妥协》),或是作者对某个事件意义的主观引导(奥利佛•斯通的《刺杀肯尼迪》),但是《大象》既没有核心人物命运的揭示,也没有对事件原因和影响进行全景分析,而是选择了没有表演经验的高中生和一所与哥伦拜恩中学相类似的中学校园,用摄像机跟踪了多个主人公在惨案发生前几个小时内在校园里的活动。
加斯把惨案变形为一个复杂的叙述线团,高中生、老师、少年杀手和受害人,影片从开始就在只有中学才能提供的场所里,对每一个人展开了一段段长长的流动跟拍,记录了一所中学普通的日常活动:食堂、操场、教室、走廊、厕所、体育馆和图书室,逃学未遂被父亲带回学校的约翰,喜欢摄影的艾利亚,因身体残疾而感到自卑的米歇尔,正在热恋中的乔丹和凯丽,尼科尔等三个说三道四的女孩子,还有上课时收到欺负的埃里克。这些人物、环境看上去与其他类似主题的电影差不多,而影片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以不同的人物视角观察在同一场所发生的活动,从而使日常事件暴露出经验性的繁复、驳杂的真实面孔。
表面上看起来线索错综复杂,主人公众多,实际上加斯的思路非常清晰。他以两个固定时间作为电影的起点和终点,影片开始的真实时间是埃里克上课时受到同学欺负,这是枪击事件的导火索,影片终止的时间是埃里克杀害最后两个藏在冷冻室里的乔丹和凯丽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不同主人公的活动展开了关联和交叉。影片一开始是“约翰部分”,他跟着父亲坐车回到学校上课,摄影机跟着他在教学楼里活动,接着是“艾利亚部分”,他到校园边的树林里照相,打算回到学校冲洗底片。两个人在走廊里相遇,艾利亚给约翰拍了一张照片。加斯先在“约翰部分”描述了这次相遇,又在“艾利亚部分”从相反的方向重新演示了相遇,他们相遇时,米雪尔从艾利亚身后偷偷地跑过去,所以范.桑特在“米雪尔部分”第三次演示了这次相遇。
就这样,摄影机跟着不同人物在这些固定场所里展开了交叉,每一个段落都是一个人的活动片段,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成为对方的“经验片段”,然而,仅仅是一个片段,只有把这些片断连缀在一起我们才得到了一个完整的时间。这说明对于枪击案,每个当事人都只看到了这个事件的一部分,“艾利亚部分” 在影片中的结尾是他洗印照片之后到图书室借摄影书,“米雪尔部分”的最后一个细节是她走进图书室往书架上摆书,突然听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声音。影片直到叙述“埃里克部分”(杀手之一)时,我们才知道上述两个结尾是艾利亚和米雪尔被埃里克打死之前的最后活动,米雪尔听到的声音是埃里克拉枪栓的声音,米雪尔和艾利亚是他最先打死的两个人。在这些同学中,只有约翰幸免于难,他走出教学楼时正好看见埃里克和阿莱克斯走进教学楼,他在教学楼外面还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这与这两个同学有关。在操场上,甚至有人认为是失火。因而,观众跟随每个当事人的活动(实际上是片段),就好似一个摸象的盲人,只看见整个事件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种效果,加斯在每个人物的身后对他们进行了近焦跟拍,所以当人物在走动时,周围的景物都被镜头虚化了,最大限度地再现了当事人的“可见度”,对每个人经历之外的情节没有做任何叙述,这样才能不断地触摸、发觉事实的真“象”。
除去影片特有的叙述,青少年的校园生活和在他们之间存在的问题也一并得到揭示。影片没有任何主观评论,包括杀人的动机,枪枝的来源,对美国枪枝管理的松懈、日渐暴力化的传媒和电子游戏也没有评判,当埃里克和阿莱克斯通过互联网买枪时,电视里正在放希特勒的纪录片,阿莱克斯在玩一个第一人称的杀人电脑游戏,但这一切似乎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唯一有主观感情流露的画面是两个孩子杀人之前在一起淋浴,埃里克对阿莱克斯说“我亲你一下吧,我从未亲过任何人。”在社会中,中学校园作为现代社会里的一个机构,就像在这部美国电影中一样,它同时还是一个幻觉工厂,一个学着服从权力的实验室,一个有着独特逻辑、秩序和欲望的隔离区,教育成为一个形式的虚设,成年人没有从根本上理解这个世界。孩子们的伤感、憎恨、幼稚和孤独,这个“问题年龄 ”从未获得一个合理的解决。加斯为了拍摄访问了许多学生,他说,“有的中学生认为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也有的则很满足,但有的人直接说校园生活就是地狱”(引自《大象》法语版海报)。校园隐藏的这些问题就像一枚炸弹,这部电影拔掉了它灾难性的引线,当埃里克和阿莱克斯决定以自己的逻辑和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时,他们对这个成人世界已经不再信任,这不但是个少年悲剧,也是成人世界和现代社会的悲剧。
综上所谈,这部被国际影评界一致称赞的电影紧密关联着两个成功因素:首先电影客观地再现了当代中学生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状态,引发了社会对青少年问题的重新重视,为此法国国家教育部2003年社教评选以绝对多数票把一等奖给了《大象》,可见该片在整个西方教育界引起的反响;第二是它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时间-空间语言挑战了传统电影的现实主义,从这个角度,讨论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哲学层面,对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实,时间已经过去,以回忆和和判断建立的感知体系能够还原事实本身吗?从现象出发如何抵达真相?经验事实是否就是事物的本质?电影的艺术虚构性与现实的真实性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个题域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始一直到德勒兹的“影像-时间理论”似乎一直在延伸,加斯想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任何理性,无论是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还是纯粹的理论/话语推导,在现象的丛林中是多么盲目和无知。他说,“我就像哥仑布,我对一切将一无所知”,也许正像《疾走罗拉》的开场白那样,“电影只进行90分钟,剩下的都是理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