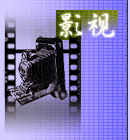| 编者按:老上海,金嗓子,花样年华,构成了我们对这个女人回忆的方式.她的繁华落尽,她的红颜旧事,勾起我们多少绮思.让一切在静静的怀旧中泛漾开来。 |
|
“啪”的一声微响,碧绿的台灯被一只素手扭亮。细微的光线旋即投入壁纸的紧紧怀抱,在这个暧昧的立方体里,烟雾止不住地缭绕,它正努力想把情人旅馆变成个家,暖暖的,叫谁都舍不得先走。
开始的时候,男人一样的大提琴轻拨细捻,焙烤出焦黄面包的醇香味道,那低音贝司温文地挑逗着、试探着,不迫切,但也不矫饰。
终于,他还是等来了优伶般的中提琴。
艳若泣血的迤俪旗袍、婉约愁怨的美丽面孔,娇媚的高跟鞋正一步一步地踩进他的心坎里。
这难道是1962年的香港吗?没有洋人、洋车、小弄堂、旧皮箱……只有一幕应该被默许、被纵容的“偷情”。
一把贝司和一只提琴的。一根香烟和一件旗袍的。
《花样年华》中的周慕云,是很多男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他头发光滑、一丝不乱,腼腆的笑容下,有着刀锋一样的下巴,优质地让别的男人相形见绌。
经常的,周慕云轻叼着一根烟卷,微抿的嘴唇还来不及翕动,暗白的烟灰就像爱情一样,扑簌簌地落下。落在看不见的地上。
当然,还有被烟雾紧紧缠住的苏丽珍。
她把种种的委屈拼命地塞进高领旗袍里,用天鹅一样的姿态和自己对抗着。一个恪守妇道的丽人儿,突然想让自己轻佻的时候,那美丽往往是摄人心魄的。
花样的年华
苏丽珍毅然地说:“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然后,她不停地变换美丽旗袍,努力不看刚刚被埋在衣服里的爱情。因为那残留于锦缎上的烟草味道,只能让她想哭,一次又一次的。
一直困惑于肉体与灵魂的无法相偕而生,因为它们该是多么无关的两种概念啊!但此时,它们却因了爱情的一味挺进,四散了,含混在坚挺的表情之下,幻化成更多的小点,慵懒却不容置疑地占据着各自的心扉。
……
贝司和提琴已经开始谐奏,而香烟和旗袍还在隐忍着。
香烟担心剧烈燃尽的烟头会烫伤手指;而旗袍害怕自己的柔软禁不起一丝一缕的灼烧。
他们只好各自在原地结网,一圈比一圈大,一圈也就比一圈难走。他们都希望可能越界轻触,但又深知对方的网同样脆弱、没有把握。
于是,这两张孤伶伶的网只能无限蔓延、扩大,但始终不得交错、圆满。
故事到这里,竖笛过来了,钢琴过来了……在歌声鼎沸的最高处,低音贝司也顺理成章地退回到他最初的稳重,漠漠地听完中提琴最后的一声叹息,便离开。像所有偷情的结束。
至于相拥在橘红色里的张曼玉和梁朝伟,除了诡谲的王家卫,大概没有人会想到更好的办法帮他们撤退。
他让吴哥窟的一个树洞收留了周慕云的烟灰;而寻进周慕云旧居的苏丽珍,也在最后一件旗袍的温情掩护下,收回了那双绣花拖鞋。
还好,墨镜后面的王家卫只是用孩子一样的无邪,成全了人们的妥协。除了“2046”号的空房间,他没有给故事残留下一丁点悬念。
因为真正的爱情还不会赋予他这种资格。
但这又是真正的爱情吗?你与我。我与他。她与你。还有他与她。
爱情不再是一个点,一条线,而是一个面,一个谁都不忍心剪破的圆。两个,不——应该是四个,四个坚贞的男女负着各自的“十字”,一起和爱情打架。打到面目模糊,打到那么的不堪,打到谁都看不见花样的年华。
为什么老藏在旧式留声机里的周璇会唱得那么远? |